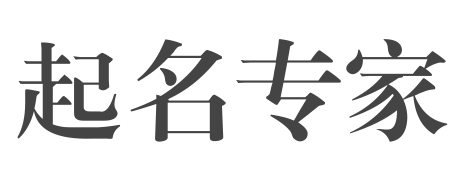陈善伟: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者和宗教思想研究
时间:作者:起名专家
陈善伟: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者和宗教思想研究
译者说明本文是海外学者陈善伟留下的一篇论文(英文),译供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者和宗教思想研究者参考。
本文共二部分,全译第一部分(约八千字)论《仁学》与佛学的关系;节译第二部分(约二千字)关于谭嗣同哲学思想的争论。这里刊登的即第一部分。作者认为,谭嗣同在发展“仁”的哲学概念方面有贡献,但也指出把“仁学”与佛学概念简单类比的缺陷。不论把谭划为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都会犯无视其主要概念双重性的错误。实际上,佛学思想并不是谭的消极因素。
由于宗教知识和翻译水平有限,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谭嗣同(1865-1898)是现代中国一个丰富多采的人物。虽然他的生命极为短暂,但他在中国历史上却起过重要作用。他的主要论著是《仁学》,梁启超称他为“清末知识界的泰斗”。有的史学家称他为“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激进思想家”。
《仁学》实质上是一部比较政治学、比较宗教学和比较研究学著作。谭将中国与西方比较,指出它的弱点与优点。他的论断建立在形成他的著作的基础的主要概念上面。在形成这些概念时,他想综合中国与西方不同学派思想为一体,但是,他未能建立一个合乎逻辑的哲学体系。他的思想中存在着矛盾与冲突,反映出一个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理状态。他既墨守全盘西化,同时又坚信中国文化,特别是佛学的生命力。谭最亲密的朋友梁启超以“实用佛学”来说明他整个的思想体系。梁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他“又治佛教之‘唯识宗,‘华严宗’,用以为思想之基础,而通之以科学。”
然而,谭政治思想里的佛学作用并小象看来那样明显,由于论说中的矛盾使得人们对于影响他的政治思想形成的上要学派作不同的解释。细读《仁学》,表明谭并未将各学派简单拼凑为一个大杂烩。他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者,他尽力从各学派吸取精华的东西,形成一个有效地建立在佛学哲学基础上的综合体系。因而《仁学》中所有主要概念都深深地浸透着佛学思想。本文拟探索这些概念的佛学基础,但是,并非不重视其他史学家评论各学派思想的重要作用。
首先,《仁学》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第一,论述全篇玄学基础,即:仁、以太、通和心力;第二,考察评论困扰中国的主要问题;第三,佛教、孔子、耶稣三家学说比较。《仁学》以二十七界说开始叙述。详述界说需用很长的篇幅。第一部分,撇开谭对时事的批评,则首先是关于“仁”“通”和“以太”的解释。凡与阐明主题结构相关之处,都将引用“界说”。
头两条界说叙述谭的么学实质。谭写道:“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第二条界说是“以太也、电也、粗浅之具也,借其名以质心力。”由此可见,“仁”是“通”最根本的来源与实质,“通”的原则藉以表达的工具就是“以太”“电”,首先是“心力”。
这四个概念中,“通”是最重要的,但又是成问题的。这个中国词在不同情况下可有不同含义。它可以表达“统一”“一致”“通达”“交流”“渗透”“通过”“充满”或“无碍”,问题在于这些英语同义词的性质和派生词义的词源。在本研究论文中,我确认“通”这个概念,首先是由强调各方面互相兼容并包的华严佛学中吸取来的。更明显的是谭在界说三中把“通”作为“仁”的特性。他说:“通之义,以‘道通为一’为最浑括。”谭氏词汇中的“道”即是“仁”的同义词。下面一段话说明“通”和“仁”在某些方面是相关联的:
“是故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异域如一身也;故易首言元,即继言亨。元、仁也。亨,通也。苟仁中国文化概论中的佛家思想,自无不通。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
“仁”的另一个特性是它的社会和政治含义。界说四最简明地叙述了这一点。谭认为“通”能够在四个不同方面起作用:
“通有四义:中外通,多取其义于《春秋》,以太平世远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多取其义于《易》,以阳下阴吉,阴下阳吝,泰否之类故也;人我通,多取其义于佛经,以无人相、无我相故也。”
但是,谭又说,“人我通”这个取自佛经的无所不在的概念,可以归入其余三个含义之内。川谭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终括其义,曰‘人我通’。此三教(佛、孔、耶)之公理陈善伟: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者和宗教思想研究,仁民之所为仁也。”按这段原文引语判断,他可能是引自《金刚经》。然而,这种无我的教义是一切佛学宗派的共同原则。如同在《仁学》中所见,否定人我的存在被用来证实佛学“再生”的概念。

整个佛学中的“通”与华严宗的“无碍”相同。华严宗是建立在理法界普遍因果律基础上的。按照这个因果律,众生同时显现。但是,一切皆空。“空”有作为本体的静态方面和作为现象的动态方面。本体与现象必定互相无碍地混为一体,一切现象都相互同归。因而,每个现象都是它的本体的表现,但是,它又区别于本体。主要观点是一切现象都是本体的表现,而它们义互相完美地协调一致。谭从华严佛学中引出的是《仁学》最重要的原理,即他用以阐述各个现象的相互渗透,相互兼容的“通”的概念。象华严佛学一样,谭也讲四个“无碍”,但它们是不同的,前者是玄学,后者主要是社会政治学的。
谭这样叙述“以太”的概念:
遍法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之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筦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嗅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
依他看来,“以太”是众生之源。它使身家天下相维系而不散去。它能使人身有感觉,使世界的分子粘着而保持平衡。在这个宇宙体系内,有一个由天地万物组成的等级世界,世界海,世界性和华藏世界。此外,还有“算所不能稽、而终无有已时”的永远无限的极源。
谭义说,“以太”至精微之作用可见于人脑与虚空电功能之中。他还认为,脑为有形质之电,它必为无形质之脑。脑气筋之周布,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贯穿如电线之四达。谭又说,既如此,不同实体无差别。在人我之间有差别的是“不仁”。因此,“仁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那么,这里就存在着“仁”与“以太”之间的紧密联系,这是谭从未清楚地研究出来的。他在《仁学》中一处说“夫仁,以太之用”,在另一处又说“天地间亦仁而已矣”。故“学者第一当认明以太之体与用,始可与言仁。”
“仁”与“以太”之间的关系,也许在佛教玄学中更好理解。谭在界说十一中说:“仁为人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他在界说十三中又说:“不生不灭,仁之体。”这样,“仁”实际上就是“唯识”佛学中第八识的同义词。“心力”,作为实现完全协调一致的意识境界,比“以太”和“电”提供更可用的工具,就是仁力。这在界说十二中很明显:“仁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有这些都说明仁是佛学的终极实体。作为本体的“仁”比物质的“以太”更高超。然而,从现象世界方面看,“以太”是精炼微妙、不生不灭的粒子分子。所以,仁让“以太”保存它原有的作用——世界万物互相渗透兼容并包的作用。
谭关于“仁”的阐述,对发展这个哲学概念作出了两点贡献。首先,他提出“仁”的意义与存在最原始的成分“以太”相关联。“仁”义贯穿世代,由具体德行臻于普遍完善。他说:“天地间亦仁而已矣。”他背离传统解说,使“仁”和“以太”一致,因而给予它一个新颖的科学含义。其次,谭把“仁”作为“唯识”第八识和华严“无碍”的同义词,他写道:“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这说明《仁学》第八识思想和“仁”的创造性泉源结合得多么紧密。谭还把“通”作为“仁”最基本的含义和从华严佛学引伸出的概念,使“仁”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佛学倾向。
然而,“仁”可能为名所乱。但,仁无亡也,匪惟以太也,仁固无亡;无能亡之者也,办无能亡也。谭用佛学概念“不生不火”来解释这一点,他说,既然万物无不“不生不灭”,“名”的更改是没有意义的。“名”是人造的,“名”被曲解,人也就迷惘了。谭说,这是与佛家所述相同的。他说:“自无始来,颠倒迷误,执妄为真。”
谭在探索“不生不灭”之源时,用佛语提出了许多问题:
“不生不灭……出乎微生灭……一刹那顷,已有无量佛生灭,已有无量时生灭,已有无量世界法界生灭。求之过去,生灭无始;求之未来,生灭无终;求之现在,生灭息息,过乎前而未尝或住。是故轮回者,不于生死而始有也,彼特大轮回耳。……佛故说三界唯心,又说一切唯心所造。人之能出大轮回否,则于其细轮回知之矣。细轮回不已,则生死终不得息,以太之微生灭亦不得息。”
谭进一步想把佛学概念“三世一时”“一多相容”和“不生不灭”思想联系起来,以便消除“时”“我”之因袭观。这个原理被用来解释互相渗透的基本原则和圆融概念的一致性。这三组对立面——总相和别相;同相和异相;成相和坏相,构成所谓六相。但是,这六相不形成任何独立的存在。它们在含义上是互相依存的。这是因为华严宗的圆融概念是一个有机的、神圣的方向。
另一个概念“一多相容”表现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真释入门》中。华严的中心思想是,没有“多”,“一”就没有任何意义。《华严真释入门》写道:“一个人看到周围的微尘时,即看作微心,没有比它更微小的了。我们能看到微尘,完全是微尘反映在曾经看到过又高又宽的大山的心中的原故。所以,大寓于小之中。这个原理还可以从法藏论《金狮子章》《十玄门》之一来领悟,这是领悟一多相容和相异之门”。
谭用“三世一时”消除的另一个思想就是否认时间的客观性。《华严经》说“瞬息即万世,万世即瞬息”,时间的概念,以华严哲学中的“圆”观为转移。《华严经》又说:过去中有未来,未来中有现在,无穷的世代不过是一刹那,而一刹那即无穷世代。
但是,由于命运轮回所乱,这种“一多相容”的思想,“三世一时”的“辩证”对待,也可能由对待所乱。对待是相信我执存在的结果。这个坚持对待的错误,可由“涨也缩之,微也显之,亡也存之,尽也衍之”的西方科学有效地纠正。谭说,欲破对待,必先明格致;欲明格致,又必先辨对待。“辨对待”者西人所谓辨学也。谭把它视为学者之始基也,由辨学而算学,由算学而格致。格致实辨学算学同致于用者也。学者之中成也。格致明而对待破,学者之极诣也。从这个观点出发,谭清楚地表明他关于佛学与科学之间的观点:“西学皆源于佛学,而惟佛学可复明于世。”为什么有些人不懂或不能懂这个原理,是因为他们只用五官——眼耳鼻舌身——辨色声香味触而已。但是,很清楚,我们对于整个宇宙的认识“必不止五也明矣”。他引用《大智度论》关于五官的概念: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肉眼见与天眼见是肯定不同的。实际上“无所见而不异焉。”
当谭继续阐述和探索不可见的生灭之源时,他立刻陷入了深奥的唯识哲学之中。人们感到生灭不息,是曰唯识。即使第八识是无生灭,我相的概念是由于是第七识作用的结果,这个我相产生了第六识和可见的外相。“相”在成为未来命运的第八识中轮回发展。谭详尽精致地阐述唯识佛学,归结为“吾大脑之所在,藏识之所在也。”它们的关系如同一面镜子和它反映的影象,“两镜相涵,互为容纳,光彩重重,非内非外。”
以上说明,谭使唯识相容关系中“以太”的作用更加明确。他说:“以太亦唯识之相分”。既然只有意识存在,形就可以抛弃。因此,可以说“以太”是不存在的。这个词只不过是从佛学智慧的高度作为一个符号,它是不能说有始有终的。然而,意识确是有终。它在命运意识转成智慧时即终结。这里,谭提出了到达成功的神圣之路或究竟位之终极阶段。也就是成佛。
在同一段话内,谭对孔子《大学》与唯识宗、华严宗佛学作了详细的比拟类推:
“大学盖唯识之宗也。唯识之前五识,无能独也,必先转第八识;第八识无能自转也,必先转第七识;第七识无能遽转也,必先转第六识;第六识转而为妙观察智,大学所谓致知而知至也。佛之所谓知意识转然后执识可转,故曰:“欲诚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藉乎格物;格物致知者,万事之母。孔曰:“下学而上达也。”朱紫阳补格致传,实用华严之五教。华严,小教小学也,非大学所用。其四教者,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中国文化概论中的佛家思想,始教也;“以求致乎其极”,终教也;“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顿教也;“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圆教也。无论何事,要必自格物致知,此之谓妙观察智。第七识转而为平等性智,大学所谓诚意而意诚也。佛之所谓执,孔之所谓意。执识转,然后藏识可转……第八识转而为大圆镜智……前五识转而为成所作智……藏识转,始是以为仁。……至若前五识皆转,无所往而非仁。
……且夫大学又与四法界合也:格物,事法界也;致知,理法界也;诚意正心修身,理事无碍法界也;齐家治国平天下,事事无碍法界也。夫惟好学深思陈善伟: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研究者和宗教思想研究,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也,即未有能外佛经者也。
谭想证实的是佛学包涵着体现在孔学中的全部原理。他指出“格物”和“致知”即深思熟虑的智慧成就,分别属于事法界和理法界。诚意、正心和修身,分别同等于平等性智、大圆镜智和成所作智。它们共同与理事无碍法界“相应”。成所作智生仁,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化。它又是事事无碍法界的同义词。
试图探索和等同佛学与孔学系统中的意识的演变和智慧的成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失误。例如,谭在上述引文中,把《大学》中“格知”一段里的每个句子都与华严宗“五教”之一相类比。这种类推比拟是站不住脚的。“五教”,首先是把所有的佛学教义或学派批判地划为不同的阶段或时期,显示《华严》是佛教中最丰富完美的学说。因此,它常常被称为“大乘圆教”。这种划分部分地来源于中国知识传统的广博性。谭著从未提及的天台宗也有类似的划分,但是所用的标准和术语是不同的。如果说,谭可以对华严进行这样的类比,那他同样可以对天台宗或其他任何佛学学派进行类比。然而,主要困难之点在于这种对应是不适当的。简言之,谬误在于“扩展知识”即获得知识过程的解释,而“五教”是佛学学派划分的基本内容。
当我们把《大学》的主要原则和八种意识转化为四个先验的智慧以及四界相比较时,我们可以看到,谭又把孔学精神文明阶段和“法界缘起”的本体概念以及由八种意识发展而来的“智慧成就”混淆起来。但是,谭从这个分析中真正领悟到了他著作中“仁”思想三个体系的共同普遍因素。这说明,为什么谭把“仁”看作“唯识”,以及这种思想怎样与整个事法界“无碍”概念相关联。界说十三说:“不生不灭,仁之体。”其它关于仁的界说,如界说一:“仁以通为第一义,”界说十七:“仁一而已;凡对待之词,当皆破之”,这就会立即很清楚地把它当作华严佛学了。上述讨论也揭示了谭对孔学与佛学哲学进行类比的错误。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谭后来试图对佛学与科学进行另一个类比。
心力是四个主要概念中最末一个概念。谭后来在第二部分讨论平天下的适当方法时,开始发展了这个概念。谭悲愤地说,他忧虑中国之命运,不禁想到一场大灾难迫在眉睫。因为国人皆无善意。他说,西方用机器制造货物,国人用心培养祸害。机器由猜疑忌妒而生。这必须放在一边,以便挽救中国免于濒临危亡的灾难。谭建议说:“无术以救之,亦惟以心解之。”
伟大的心力确是无所不知的。但它还有否定的方面。心力如果用得不当,原本是平机心之心力就会转化为机心。解救法在于懂得,心力之实体,莫大于“慈悲”。谭说:“慈悲,则我视人平等,而我以无畏;人视我平等,而人亦以无畏。无畏则无所用机矣。”心力,可用来拯救中国,也可拯救全人类。谭说:“以心挽劫者,不惟发愿救本国,并彼极强盛之西国,与夫含生之类,一切皆度之。”谭又说:“以此心为始,可言仁、言恕、言诚”诸美德。这可是富于感染力的。谭对于拯救世界寄希望于“以感一二人而一二化,则以感天下而劫运可挽也”。“盖心力之用,以专以一。佛教密宗,宏于咒力,咒非他,用心专耳。”谭还提到十八种机械动力以表示极类似《华严经》佛家的“十力”的心力。
谭倾向于将佛学与科学联系在一起,又表现在他解释人我之间缺少沟通是由于脑气运动差异之故。他说:
其动者,意识也,大脑之用也。为大脑之体者,藏识也。其使有法之动者,执识也;小脑之体也。为小脑之用者,前五识也。惟睡梦疯癫,辄为无法之动,意识未断,而执识先断也。执识亦非断尽,我执未断,而法执先断也;大脑明,而小脑半昧也。唯识所谓昏沈举第七识,暂断者也。夫断识本有实序,先意识而后执识,先我执而后法执;……夫脑气动法,既万有不齐,意识乘之,纷纭而起。人与人,地与地,时与时,事与事,无所往而不异,则人我安得有相通之理?凹凸力之为害,即意识之为害也。今求通之,必然意识;欲断意识,必自改其脑气之动法。外绝牵引,内归易简,简之又简,以至于无,斯意识断矣。意识断,则我相除;我相除中国文化概论中的佛家思想,则异同泯。
还有另一个将唯识八识与大脑小脑作用勉强类同比拟的例子。第八识和意识,分别为大脑的体和用,而藏识和前五识分别为小脑的体和用。谭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继续描述接受映象怎样与八识作用相类似,意识怎样导致体现心力和最大的成仁。换言之,仁是通过抛弃我相与法相的错误信念达到的。上述引文中,谭实际上试图用“心所有法”来解释梦的形成(“更有新法,可测知其所梦为何梦、山是即可以器造梦,即照器而梦焉”)。人们由此可见,这种心之概念,都显示出佛学与西学的影响。心力与唯识中第八识相一致。根据最新的研究,谭还从约翰·弗莱尔翻译亨利·伍德的著作《脑影显象》中吸取了《治心免病法》。
然而,史学家对于这些主要概念的关系与性质的看法是有广泛分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史学家认为,在确认谭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之前,弄清这些问题至关重要。非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大多数在海外,却不大关心谭在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这类问题。一本论谭嗣同的、马克思主义的专集表示了研究谭嗣同思想的巨大兴趣。1954年,《谭嗣同全集》出版,引出许多文章专论研究谭的政治文化思想,和讨论谭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1958年,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由于《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三卷至1960年第一卷)发表了迄至当时为止尚未发表过的谭嗣同的某些文章,使研究谭嗣同的兴趣更加浓厚起来了。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关于谭嗣同的研究,带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两方活跃争论的特色,他们对于《仁学》之主要概念的性质各持不同的观点。
方允臧译
由起名专家专业的命理起名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