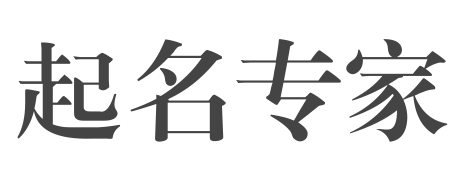干春松:两岸新儒家见面怎么掐蜀山会?
时间:作者:起名专家
干春松:两岸新儒家见面怎么掐蜀山会?
【按】2016年1月9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在成都杜甫草堂举行。围绕着牟宗三与康有为、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儒学与现代性、儒教文明与核心国家、国家国族建构与儒学实践等主题,港台学者李明辉、林月惠、陈昭瑛、谢大宁、郑宗义,与大陆学者陈明、干春松、唐文明、曾亦、陈壁生展开辩论,交相问难,其文字实录登载于主办方《天府新论》今年第二期。以下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的发言实录:
【前情简介】
蜀山会(1)隔空舌战一年两岸新儒家见面怎么掐
蜀山会(2)李明辉正面回应大陆学者质疑 直言两大隐忧
蜀山会(3)陈明论“回到康有为” 港台学者:想干嘛?
台湾学者林月惠:儒学为东亚所共享 非一姓一国独占
曾亦:大陆与港台新儒家的不同之处在两大方面
唐文明:从儒学复兴看康有为与牟宗的异同
主持人李清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各位老师早上好!经过昨天的深入讨论,我们这个会议现在已经初步达到了预定目标,也就是开诚布公,深入讨论,达成共识。当然,我们现在所达到的共识还只能是初步的,不可能在一两天之内就让双方完全莫逆于心。甚至可以说,我们这个求取共识的过程乃是一个无尽的过程。因为两岸儒学之争,不仅仅牵涉到问题意识、理论视域等方面的差异,也意味着对于整个现代儒学的理解和认识不一样。
如果我们把现代新儒学、港台新儒学以及大陆新儒学都纳入现代儒学,那么可以说,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于现代儒学的理解,或者说现代儒学的自我理解,一直就处在一个探索过程之中,这种探索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这次两岸儒学对话,其实就是现代儒学关于其自我理解的一种交流。对此,我们可能首先需要反思,我们是不是以属于儒学自身的方式来理解现代儒学?现在谈论现代儒学,之所以在很多方面出现分歧和矛盾,也许正是因为我们的思考不是从儒学自身出发,而是从现代各种不同的理论、话语或主义出发。我们现在谈论许多问题时,确是过分受到现代西方观念的影响。因此,要想在两岸儒学的对话与交流中达成更多的共识和理解,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现代儒学是否达到了足够明确和自觉的自我理解。
现代儒学的自我理解包括好些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现代儒学究竟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对此,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加以思考,比如陈明从宗教角度,唐文明从文教、教化角度来立论。而在我看来,也许更应该把现代儒学看作是现代中华文明之道的核心,也就是现代中华文明的“常道”。我们讲现代儒学是“常道”,意味着它与一般的学说、理论或主义不是同一个层面,而是更高、更全也更基础的东西。“道”是全体大用,包括“理”,但远远不止是“理”。
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每一种文明都各有其“文明之道”。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中华文明,都是如此。俗话说,“蛇有蛇道,鼠有鼠路”,根据中国学术传统,万物莫不各有其道,各有其存在根据和存在方式。作为相对独立的庞大生命体,每一种文明也都基于自身的条件、境遇和历史传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其生存发展之道,即“文明之道”。“文明之道”是一个整体概念,包括多个层面和多个方面,既包括一套基本的观念(如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真理观、价值观),也包括一套相应的规则、制度和生存实践方式(如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社会运作方式),还包括一套相应的经验、技艺、智慧、习俗等。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呼应、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因此,每一种“文明之道”都自成系统、自成一体。在不同的“文明之道”之间,当然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启发,甚至可以相互共享很多东西,但它们毕竟是各成一体,各成系统儒家思想是啥,不可能完全替代和覆盖。正如两种语言之间,尽管可以互译、互借、互渗,却终究是各为一体、相对独立。这个观念相当重要。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才以抽象的普遍性和普世价值为由,否认中华文明有其自成一体的“文明之道”,或者仅仅只从普世价值而不是从“文明之道”的各成一体来讲中国文化传统的意义。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学习和借鉴西方,但是在评判儒学传统的价值和意义,评判现代儒学的使命和功能时,既没有必要仅从西方出发,也没有必要仅从普世价值出发。
每一种“文明之道”又都有其作为根基和灵魂的“常道”,就像共同的语言一样为该文明全体成员所共享共由,因此是彼此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凝聚、实现文化认同的基础性平台,也是各成员之间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纲维。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常道就是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主导性共识,并且往往体现为典章制度和社会礼俗,为共同体各成员所“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正如熊十力所说,“夫常道者,万变所自出也”,所谓“常道”并不是说永恒不变,而是说具有更高的普遍性,能够成为其他各种学说和言论的“大地”。就此而言,“常道”也可以称为“大道”。任何一种文明内部,既有无数“小道”,也有贯通所有“小道”的“大道”或“常道”。
由此来看现代儒学,它的历史使命实际上就是要力图成为现代中华文明的“常道”,也就是仍能像传统儒学那样,成为塑造中国人之精神世界、价值体系、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全体大用之学。我们这样说,主要是基于四点考虑。首先,从历史传统来看,儒学本来就是近两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常道”。其次,从现代儒学自身的努力来看,它从一开始就以现代中华文明的“常道”自任。再次,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华文明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虽已通过艰辛努力建成独立国家,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完整建立起自主自适的现代文明之道,而在目前尤为迫切的是需要建立其“常道”。能够承担此任的,只可能是由有着悠久传统、深厚基础、丰富经验的儒学传统转化出来的现代儒学。最后,从全球现代化运动的进一步展开来看,也要求作为“儒教文明”的中华文明建立其常道,从而建立起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文明之道。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现代性观念的分殊化过程,也就是各大文明依靠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自建其现代之道的过程。一向被视为儒教文明的中华文明只有以现代儒学为其“常道”,才能真正建立其现代之道。
刚才讲到,“道”不只是理,而是包含多个层面、多个方面的全体大用。因此,现代儒学要想真正成为现代中华文明的“常道”,就必须发展出多个层面和方面,成为全体大用之学。事实上,在中华文明建构其现代之道尤其是现代“常道”的过程中,现代儒学已经自然而然地开展出了四个层面。首先是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期间开展出较为边缘的“技”与“学”的层面,其次是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期间开展出较为核心的“政”与“教”的层面,然后是“五四”运动以后逐渐开展出来的最为核心的形上之“理”与“道”的层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相当重要、作为社会构建之基础的“礼”与“俗”的层面,虽然还没有完全开展出来,但现代儒学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努力,尤其在近年的民间儒学中已经初现端倪。由现代儒学自身的这一发育过程来看,它确实是既需要哲学的层面,也需要宗教的层面,更需要政制、礼俗的层面,当然也包括身心修养等等层面。就此而言,港台新儒学和大陆新儒学,确是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不同进路的关系,但这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并列、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关系。由于时代条件和现实机缘的不同,我们不得不对于其中的某一层面有所偏重,但这并不意味作为全体大用之学的现代儒学本身可以有所偏废。尤其在今天,现代儒学的建构已有条件从不同层面来同时展开、齐头并进,没有必要是此而非彼。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今天的儒学发展与建构,如果仍停留在被叙述、被解释、被规范的层面,而不能积极主动地以现代中华文明的“常道”自任,在建构“现代中国”乃至现代世界中努力充当叙述者、解释者和规范者,便可谓是昧于时势、不识时务。
总之,如果我们对于现代儒学有足够的自觉,那么两岸儒学之间的对话将可以达成更多也更进一步的共识。
以上是我的一个简短的引言。下面首先有请北京大学干春松教授发言!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
干春松:重温贺麟先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
我挺接受郑宗义老师的一个说法干春松:两岸新儒家见面怎么掐蜀山会?,他希望这个会是一个互相走近的会,他以前做过文学工作,所以我觉得他的描述很生动。经过一天的会讲,我觉得的确是在互相走近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我提交的发言提纲是重温贺麟先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其实,这只是一个话头,我最近阅读他的一些文章是想知道一个十分了解西方的学者,是如何来处理儒学的“现代性”问题的。我最近还在看他的1940年关于五伦的讨论文章,唐文明他们也都关心过,后面就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这篇文章。
我今天主要是想讲五个问题,都比较宽泛。第一个问题是儒学与中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是这两天讨论的一个特别大的背景性的问题,尤其是因为昨天唐文明关于需要有一个核心国家的说法引发了一些争论。这个话题的起点,是因为贺麟先生在那篇文章里面一开始就是有一个特别直接,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震撼的说法,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他说:“民族复兴不仅是争抗战的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自由、独立和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份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
类似的话,我们现在经常能听到,即使是政治领导人也如此说,尽管他们不会直接说“儒家文化的复兴”,但会说“民族复兴是一个文化复兴的问题”。关于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这个问题,从1920年代开始学者们就比较喜欢讨论,实质是中国之所以是中国的问题。当一个新的国家逐渐建立起来之后,这个问题自然会产生。也就是说,你所理解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你所理解的中国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仅仅是一个地理范围内的国家,还是一个文明国家?而对一个儒者而言,所谓的文明国家主要指的是一个儒家文明的国家,这是一个特别带有信念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21世纪以后,在大陆的话,我昨天也说过新儒学的一些议题,是在跟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展开的。那么这个争论,其中一个很焦点的问题就包含了对这个中国的理解,就是要立成一个什么样的国的理解,就是我们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理解。
当然,我个人也尊重自由主义等对未来中国走向的理解。其中很多的自由主义者都是我们的熟人,他们中有些人认为国家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保护每个人的权利。既然有一部分人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生活,那让他自己生活就行,这也是一种对国家的理解。新左派也有他们对国家的理解。
我们可以体会一下,贺麟先生为什么认为抗战救国不仅仅是一个抗日战胜的问题,而是要有一个更大的目标,那就是要儒家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的前途,这是一个基本的入手点的问题。但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现在大家不再特别具体地讨论,而是把它转变为学术性的讨论,就是如何解释中国。像2004年前后我们讨论合法性的时候,经常会展开这样的一个问题。
关于儒学对中国的理解是否会导向民族主义和霸权国家的问题干春松:两岸新儒家见面怎么掐蜀山会?,我觉得有一些人的论述可能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更多的学者是从王道政治和天下体系来理解儒家的世界秩序认识的。我们最近也看到葛兆光在《思想》里面发的那篇文章。我觉得葛兆光的文章最后的结论是蛮有意思的,他说中国人现在在讨论的那个天下主义事实上是民族主义的一个变相的反应,最终还是要争谁做老大的问题。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老大不老大有时候不是争的问题,而是说它有一个使命。有些话说起来是不好听,不过你也得承认,一些小的国家,文明特征不明显的国家,它就不存在这样的使命,它就不存在文明担当的问题。对于儒家而言,这个核心国家它是有前提的,但是它不是天然的,它不是必然的,就是“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嘛。如果有一个国家,它已经发展出更为完备的一个儒学的体系,或者说在儒学义理下,它发展得更充分、更彻底、更令人信服的话,那它就成为儒家文明的一个代表国家,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我们处于这样的一个境地里的国人,或者说学者,或者说儒者,我们自己有没有试图获得这样一个核心文明代表者的地位的追求和信念。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这涉及到怎么来理解东亚儒学,或者说港台儒学和大陆儒学的问题。
其实我自己也很不喜欢大陆儒学这样的一个称呼。我跟唐文明经常讨论说,我觉得港台儒学和大陆儒学都是儒学,地域的这个前缀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中国一百年来特殊的政治形态所造成的。而大陆又有那么一个完全彻底否定的时期,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现在,大陆的儒学研究者开始做一些儒学原创性的工作,或者它试图应对大陆来回应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觉得反而有点不适应。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感觉上的不适应,那这个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儒学与中国怎么来理解。
第二个是知识形态、信仰形态和制度形态的问题。昨天任剑涛说了两个形态,他说牟宗三是知识形态解决得最好的,而康有为是国家形态解决得最好的。我自己倒是比较喜欢用知识形态、信仰形态和制度形态这三个问题来分。知识形态这两天也一直在讨论,儒学它到底是一个经学儒家思想是啥,是一个哲学,还是一个社会政治科学?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方式是儒学最合适的存在方式呢?这其实是一个特别麻烦的问题。因为当有一批人根本不懂经学,或者根本不了解儒家的经典,仅抱着对儒学的一个热情,就自称是儒者的时候,如何来论定他们的儒学“成色”呢?因为儒学毕竟不是一个宗教,是否是教徒有一个形式性的认定。现在我们知道,有大量的做政治学,或者做法学的人,愿意在儒家思想方面做工作,那么为啥他们不是新儒家,而必然是只有几个哲学圈里的人才是新儒家呢?
我觉得儒学的一个知识形态的展开,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回溯,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或者从梁漱溟、熊十力往康有为、章太炎回溯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探究一个儒学如何逐渐知识化的过程。我现在没搞明白为什么研究《诗经》的那些搞文学的人不能成为儒者,而那些研究《周易》,在哲学系里面讲几句性命与天道的人就是儒者,我一直没有太搞清楚这个事。
然后是一个信仰形态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宗教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信念问题。我自己认为刚才我引的贺麟先生的那段话就是信念问题,他作为一个儒者,他应该有更多的对儒学的信念,并将之转化为对于中国人该怎么生活、对于中国该是什么样的国家这样一个追索,这是一种。
至于所谓的宗教问题,的确是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这也是这两年大陆儒学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应该是一个公民宗教的形态存在,教化的形态,还是甚至是一个民间宗教的方式的存在。有一些根本否定儒家有宗教的维度,甚至认为儒教问题的讨论是对儒学的贬低。这个儒家的信念问题,不光是对别人而发,更主要是对自己的发问。就是说我们所学的这些东西,我们所学的四书五经,对于我们研究者本人而言它究竟是个什么意义。它是我们的终极价值呢,是我们的一个心灵慰藉呢,还是我们的一个学术饭碗呢?这三个维度本身都没有问题,完全都可以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在现代社会存在,比如有人说,我就是做儒学的,我就是在大学里教儒学,这并不构成一个问题。问题是儒者应该有更多的担当。
刘笑敢先生曾经说一个人可以有三种身份:学者、民族文化传播者、信仰的坚持者,刘笑敢最担心的是大陆的学者经常是这三种身份混在一个人身上,按俗话来说就是“不专业”。但是我说其实你很难分清楚你研究某一个问题、推进某一项事业,是使命感使然还是学者的工作。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林月惠老师他们做《四书》的中学课本,当你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是认为这些知识对他很重要,还是认为学了这些以后对他的人格培养很重要?这两个东西功能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学校里面该不该培养价值观,或者说该不该培养一个有特殊导向的价值观,儒学是不是一个有特殊导向的价值观,我觉得这是一个信仰形态的问题。
最后是一个制度形态的问题。昨天陈壁生也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得挺好的,就是说儒学复兴如果只是习俗层面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复兴有没有必要,这个复兴的意义在哪里。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存在的方式的问题,那这个方式的问题,在贺麟先生那里或者是在牟宗三先生那里,它其实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儒学跟科学的关系。而在现在更为突出的是如何理解经学的问题,这是儒学的基准。
第三个,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儒者。唐、牟、徐,或者说钱穆先生说要为故国招魂的时候,这个招魂者的使命是他自己赋予他自己身上的。那么多的研究者,那么多的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没有几个人说他有这个招魂者的使命,或者他们也感觉到花果飘零,但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我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是我有一次去川大做讲演的时候,我刚讲完高小强老师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认为自己是儒者吗?这是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分为两部分,就是说,我说我是,我有一个不敢担当的问题,就是我够不够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不是一个自我认定的问题。说实在的,我经常唯恐玷污了这个名号。以前余英时先生写《钱穆与新儒家》的时候,他讨论的问题不就是熊门这个系统和钱穆先生的不同。在许多不同的里面,他特别强调了道统的问题,就是说他认为熊系因为有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所以钱穆先生反而怎么怎么着。那么我们不管钱穆先生到底有没有,但是起码在余英时先生的区分里面,对广义新儒家和狭义新儒家的区分里面,他特别强调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这一点。那么,当我们说谁是这个时代的儒者的时候,我们要去考虑信徒和研究者,要去考虑这个广义和狭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读徐复观先生的文章,就是唐、牟、徐那一群人里面,我最喜欢看他的那些散文。我其实就是喜欢徐复观先生那种感觉,那种承担这个时代要给他的那个使命的感觉。
第四个问题是所谓的代际的问题。刚才李清良兄也说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它到底是个并列,还是个替代的问题。唐文明曾经给过一个说法,就是他比较喜欢的是一个代际的划分,而不是区域的差别。我自己也认为从区域划分是一个不太合理的东西,就是说熊十力和梁漱溟开端,然后三代四群,这是刘述先先生也比较接受的一个划分。我经常质疑这个划分,我说这个划分从地域上来看越来越远了,第一代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第二代是唐、牟、徐,第三代就是海外新儒家了。我说越走越远了,前面还在大陆,然后到了港台,第三就是海外了,郑宗义老师应该最熟悉他们那些文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所显示的。那么问题是有没有可以有第四代,到第四代的时候,是否只能从海外,或者港台去找?我觉得原来那种太强调区域的分法,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儒学群体的分离是政治的问题,走近是一个信念和信仰的问题。走近不是一个互相体谅,或者互相了解对方的问题,而是说两岸三地的儒学研究者可能问题意识不同,但又是在为一个同样的事情在做。
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因为这个话是我在贺麟先生这篇文章里有特别深的体会。贺麟先生说“五四”那些批儒家的人对新儒家的好处实在太大。他说:“表面上,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的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的回光返照,是其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却殊少直接的贡献,反而是“五四”运动所要批判打倒的对象”。这是贺麟先生的一个表述。
贺麟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是现代新儒学最重要的贡献,它的贡献要超过张之洞这样的人。那么这个问题恰好也是目前在大陆讨论得比较多的,大陆讨论的选项里面是张之洞,还是康有为。就是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说是熊十力、梁漱溟,还是康有为,而是它并列的一个选项,是张之洞,还是康有为。2015年,我们在华东师大儒家思想是啥,在复旦,开了一系列的会,核心就是该如何重新反思“五四”对于现代中国思想和对于新儒学发展的那中间的意义。
陈明:你同意贺麟的话么?
干春松:当然不同意。
陈明:就是嘛,你必须说清楚嘛。
【精彩预告】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专题提要
陈壁生∣晚清学术重估与所谓“大陆新儒学”
摘要:今天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起码有一部分,不是在“孔孟之道-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这个脉络中来理解儒学,而是接着清末民初的经学,接过这个中断百年的传统,来理解儒学与当代中国的关系。
陈昭瑛∣新儒家、新民主、新科学
摘要:儒学应成为整个社会的底蕴,而不是大国的文化橱窗。政治与儒学应该携手合作,深化民族主义,实现审议民主与两性平权,推广环保绿能,共同贡献于中华民族的重建与世界文明的繁荣。
谢大宁∣在两岸格局下的儒学实践与自我救赎
摘要:两岸问题如果不解,台湾将永无宁日。两岸问题的撕扯,在台湾内部是以认同的方式呈现的。这个问题在台湾埋下了一个最大的冲突种子,包括两岸之间可能的冲突,世代之间可能的冲突,乃至各种不同群体之间可能的冲突。
【港台学者代表】
李明辉,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林月惠,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陈昭瑛,台湾大学中文系。
谢大宁,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系。
郑宗义,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大陆学者代表】
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
唐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
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
陈壁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主持人】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陈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李清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由起名专家专业的命理起名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