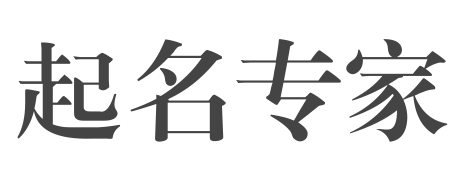:儒家文化传承下女性写作的双面效应
时间:作者:起名专家
儒家文化传承下女性写作的双面效应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人们常用儒、释、道概括其主要内容,而在这三者之中,儒家文化无疑占有支配和主导地位。由孔子集大成的儒家学说两千多年来已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统摄着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的思想意识数千年而不衰,即使有所谓的“文化断层”,也仅是理论领域的显层次断裂,在隐层次的心理层面上,它已积淀为华族人的“集体无意识”,渗入他们的心理感受和行为反应模式中。由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作家同样传承着儒家文化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棵大树上衍生的枝权,将她们的创作作为中国大陆女性写作的一种参照和比较,或许能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和把握儒家文化对于女性写作不同层面和在不同文化境遇下的同根传承与异质变奏。 一、人性化文化传承与女性写作 重视家庭人伦亲情是华人文化圈的共同特征,它在文学上表现为强调以表达伦理情感为中心及追求伦理情感的和谐融洽:儒家文化传承下女性写作的双面效应,在实际创作中,常常演绎为对亲朋好友的思念,对亲情友谊的渴望和对人伦之爱的向往,这是以家族人伦为基础的儒家文化最具人性化和亲和力的魅力之一。由于女性的生活圈子多局限于家庭之内,她们与家的关系较男性更为亲密,家庭既是女性最基本的生存领域,也是她们的生命归属。
在中华文化中,女性实际上就是家的象征,她们以自己的固守、温柔和耐心相夫教子、赡养老人、操持家务。因此,关于家的话题是华人女性写作永恒不变的母题,这一话题弥补了社会主流话语对此边缘领域的忽略。研究者们往往注意到女性创作反抗封建家庭和伦理的一面,却忽略了其热爱家庭、依恋亲情的另一面。从五四女作家陈衡哲、冰心、苏雪林等“爱的大合唱”,到新时期舒婷、铁凝的温情独吟,都如缕不绝地奏响着同一首温婉动人的亲情曲,这首亲情曲首先抒发的是对母亲、对孩子的爱。冰心的《繁星》、《春水》,陈衡哲的《小雨点》、《一支扣针的故事》,冯沅君的《隔绝之后》、《慈母》,白薇的《打倒幽灵塔》,苏雪林的《棘心》,直至铁凝的《麦秸垛》,舒婷的《呵,母亲》,林子的《给妈妈》、《给亲爱的孩子》都是这类母性之爱的典范之作。 “乡愁”是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共同母题,也是其女性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它是人类羁旅异地的一种普遍心态,蕴涵着对故土的深情和被放逐之后的回归愿望。对于有着浓厚的儒家文化家国意识传承的中国人来说,这种情感比之其他民族更为深沉和强烈。华文文学由于诸种原因被分割成几大板块,女作家们在不同的板块间由于政治放逐、文化迁徙、生活移居儒家思想的传承及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尽管在创作上都各自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特征,但其中总牵萦着一缕对故乡亲人抹不去的思念,这以被人为地与大陆阻断,隔海相望却可望不可即的台湾作家最为典型。
近半个世纪,台湾孤悬海外,40年代末赴台的女作家林海音、孟瑶、张秀亚、琦君、苏雪林、谢冰莹等都曾在大陆生活过,她们历经战争离乱、祖国分裂,暌别故园迫于无奈,欲返故土却归乡无期,隔海相望医治不了“怀乡病”,于是当她们拿起笔来时,即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丰富的心灵感受,娓娓抒写对昔日亲人师友的眷恋和对故乡家园难以割舍的情怀,这成了她们维系故土亲情抚慰内心创痛的一剂良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为我们动情地讲述着一个个老北京的故事。那色彩鲜明的红墙绿瓦,那令人陶醉的乡音乡情,蕴涵着童年的记忆,浸透着作者的刻骨乡思和“仁爱”之心。张秀亚的散文大部分也是抒写对大陆生活的回忆,在她的记忆中,家乡的“地丁花”、“寻梦草”撩人情思,家乡的“杏黄月”、“六月雨”缠绵动人。这些怀乡作品以山水之美、亲友之爱、童真之趣,表达了对亲人、对故土的挚爱,对原有生活方式的依恋和此时无所归依的“乡愁”。 然而,“家庭本位”作为农业社会的人伦传统却越来越受到当下工业文明和商业文化的挑战。现代科技和工业化发展在给人们带来物质便利的同时,也随之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如人情疏淡、身心失衡、环境污染等等,亦即导致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破坏,华文女性创作也表达了这种现代生活的焦灼与困惑。
然而富有意味的是,大陆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作家在面对这类现象时的主观价值判断不尽相同,前者多体现为对传统价值的消解和颠覆,而后者则以认同和呼唤儒家文明为旨归。中国大陆近年来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原本单纯朴实的人际关系发生了蜕变,人与人(尤其是男人和女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日益隔绝和对立。陈染和林白笔下的女主人公就大多决绝地与社会隔离,拉上窗帘躲进房间沉溺于“私人生活”。无论是倪拗拗(《私人生活》)还是多米(《一个人的战争》),无论是黛二(《无处告别》)还是老黑(《说吧,房间》),她们都一面沉醉于都市的浮华,一面又痛恨着城市的冷漠,两者间杂糅着无奈和焦躁。这种生存状况在“70年代后”出生的女作家卫慧、棉棉笔下表现得更加极端,崇尚物质消费和欲望满足成为她们作品人物生活的唯一追求,这些人除了吃、喝、睡、性交、疯狂等肉欲感知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社会维度和精神维度,读者从中感受到的只是人情冷漠、亲情难觅、爱情虚无,是失去人文精神后的一片浮躁之气。虽然大陆女作家中也有迟子建那样对纯朴大自然和善良人性的呼唤,但应者寥寥,声音太过微弱。然而,同样面对工业社会的困惑,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作家笔下却呈现出另一道风景。

同写生命的孤寂感,台湾女作家胡品清、张晓风、席慕容等以真诚、纯净、温馨的情感和笔致进行人生的解索,她们没有刻意挖掘什么哲学的形而上的意义,然而恰恰是这些生命悸动的人生体验和遐想,那种单纯宁静、平和旷达的生命意识,表达了她们执著人生热爱人间的儒家文化精神,而这正是最打动人的心灵、给人启迪和遐思、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地方。同写人性的异化,张晓风的《潘渡娜》通过克隆人事件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深切忧虑。澳门女作家玉文的《北窗外》通过“雪是白的吗?”的疑问对商品经济给人的心灵造成的污染表示担忧,这种带有女性色彩的儒家忧患意识表达了女作家们对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 二、传统文化桎梏与女性的反抗 儒家文化作为完整的价值体系,其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家庭伦理。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庭观念上筑起的。”①然而,就家庭关系而言,夫妇关系又居首位。为了使夫妇和谐、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儒家制定了一系列伦理纲常秩序,以达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但是由于政治的需要,儒家文化的夫妇伦理由一个人性化的起点开始逐渐渗入越来越多的不平等因素,以致走向了反人性甚至“以理杀人”的极端。
可见,在儒家文化中,男女地位极其不平等,女性充其量只是男人的奴仆。两性关系如此,家庭和社会如何得以和谐?所以,为着先天的性别不幸多少年来女性一直苦苦地挣扎、忍耐、斗争,终于在20世纪初,伴随着五四新文化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女作家群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等儒家思想的传承及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宣告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已不再缄默无语,她们为这一弱势性别的不公处境喊出了自己的声音,从此这声音就一直回荡在中华大地上,回荡在世界华文女作家的笔下。争取女性人格独立,冲破性别歧视和压抑,实现女性意识的自觉,成为华文女作家共同关注的焦点。舒婷的“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致橡树》)与台湾女诗人蓉子的“我是一棵独立的树――不是藤萝”(《树》),以相同的诗歌意象表达了同样的女性独立人格的意向。在文化阻隔、音讯不通的情况下,两岸女诗人竟以如此惊人相似的诗句表达了同一主题!同样,张辛欣、张洁、谌容和台湾女作家朱秀娟、许台英、周梅春等都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向处于事业与家庭、传统与现代角逐中女性的两难处境,表达了女性力争摆脱物化和从属地位的努力及所需付出的代价。造成海峡两岸女作家如此相似的创作旨向的原因,除了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及相同的女性处境外,恐怕与同根的儒家文化对女性的贬抑和相同的艺术精神的熏陶不无关系。

然而,由于受时代和社会思潮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大陆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性创作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张扬的情况又有所差异。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女性解放大多表现为历史性救赎,80年代后半期以降才进入自我救赎阶段。娜拉“出走”争取女性“人”的地位和价值是初期女性解放的模式;三四十年代女性解放又与民族解放、国家前途相交融;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解放依赖外在社会组织形式,以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为目标,女作家们多用中性话语表现时代生活,很少涉及妇女的自身问题及妇女的精神世界。至此,妇女解放一直是作为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伴随物,女性始终处于非自觉的被动状态。直到新时期,被淹没在男性话语中的女性意识终于重新“浮出历史地表”。但是,张洁、张抗抗、谌容、张辛欣等的作品在表现灵与肉、爱情与婚姻的分离和女性“雄化”的尴尬,在对“同一地平线”的质疑和“我在哪儿错过了你”的诘问及寻求女性精神拯救的“方舟”过程中,还是将女性个人的悲剧隶属于社会政治的悲剧,将妇女解放理想寄托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这一时期,虽然女性的社会参与意识较强,但女性自主的性别意识还是较弱。直到80年代后半期以来,在社会转型、中心价值裂析为多元价值的文化背景下,女作家们才开始了性别的自主觉悟和自我建构。
她们揭开历史的面纱,从父权制的根本上解读女性的命运,思考女性超政治的性别悲剧,挖掘积淀于女性深层意识中的“依附心理”,从文化和哲学的层面上思考女性自身的价值。舒婷的《致橡树》、赵玫的《我们家族的女人》、铁凝的《玫瑰门》及伊蕾的《独身女人的卧室》等开始了女性自救而非他救的精神途径探索,而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海男的《我的情人们》、徐小斌的《双鱼星座》等则更将女性自然爱欲的实现作为自我救赎的途径,宣告了女人“无性”时代和女性无话语权历史的结束。从历史救赎到自我救赎,表明女性解放已由被动的外在社会性拯救向自觉的内在精神层面的深化。从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转向对女性自身力量的审视,这是女作家对女性主体历史匮乏所进行的一次革命性填充。 相对而言,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始终较多地表现在自我救赎的层面。由于1949年前后赴台港或移居欧美等国的早期女作家大多是远离主流意识的自由知识分子儒家思想的传承及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与留在中国大陆的激进女作家相比,她们的社会参与意识较弱,带有边缘性特征,这种边缘性使她们能够以更加自由的创作姿态从60年代初开始即表现出女性不依赖于外界力量而进行自救的艰难历程。此后,随着女性主义影响的日深和女子受教育程度及就业率的提高,女性的自救意识更为自觉。
袁琼琼《自己的天空》中,静敏在丈夫有了外遇被逼离婚后,丢掉幻想,走上了独立之路,开商店,跑保险,事业有成,经济丰厚,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真爱。李昂的《杀夫》可称是力刃大男子主义的一把尖刀。林市面对有性虐待癖好的丈夫,在长期受辱导致神经错乱的情况下将他剁成肉块,以极端的方式实现了自我精神的救赎,虽然这一行为在法律上应受制裁,然而在作品所营造的特定氛围中却博得了女性群体的精神共鸣。而简赖的叙事散文《结发夫妻》中的女主人公王言则通过出家寻求宗教庇佑实现了灵魂的自赎。同样,林湄在香港时期创作的《泪洒苦行路》和定居西欧后创作的《漂泊》,印尼华文女作家袁霓的《情原是恨》也通过女性寻求人格独立和自强不息的生活道路,展示了女性自救的过程。 三、和谐的两性理想与女性写作的终极关怀 由此可见,无论是“亲情”主题的抒写或是“乡愁”意识的变异;无论对“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还是对工业文明的焦灼;无论是男女两性的对抗或两性关系的和谐,都交织着儒家文化在女性创作中的同根相承和异质变奏这两重因素。可以说华文女性创作是在既接受所在国文化的冲击和融合,又潜在地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扬弃中艰难前行的。儒家文化在华文女性创作中的这种相承和变异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表明了儒学在现代社会的演变和发展。
但无论是传统儒学还是现代新儒学,其终极理想都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身心内部、社会内部、自然界内部都达到和谐自然的最佳状态,而华文女性创作的终极指向也应是和谐:女性与亲人、与自然、与人类、与自我,尤其是与异性的和谐,所以,两者在终极目标上是一致的。然而,由于华文文学各大板块间的文化环境不尽相同,受儒文化的影响程度和侧重点也各有差异,总体来说,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性书写在对“自然”的亲和及女性书写形式上,都显得与儒家文化更为趋近,她们在生生息息中表达的中国文化精神比大陆作家更为强韧。这似乎是个悖论,依常理推,中国大陆女作家在祖先的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接受祖先的庇护荫泽,传统的积淀理应更为深厚;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作家远离故土,面临着不同文化的冲突、交流与选择,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汉文化与非汉文化的相遇,势必带来传统文化意识的淡漠稀释。然实际情形却恰好相反,究其原因,一方面,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作家由于在背井离乡的放逐中有着一种身份难以归属的焦虑,而与生俱来的血脉深处中华传统文化模式的潜在制约又使她们的思维、道德、价值观等超稳定因素在精神皈依上有着挥之不去的中华情结,所以,中华文化自然成为华文女作家创作的“灵根”;另一方面,台港澳暨海外华人妇女不如中国本土妇女对传统文化及旧礼教的压抑体会深刻,移民的流动性使她们身上没有几千年文化的重负感,更没有中国大陆那“十年文化浩劫”的痛心经历,这使她们的个人化写作不以两性征战为主要对象,言辞也并不激烈而较温和。
相比较来看,中国大陆女性写作却易走偏锋,从“铁姑娘”到“上海宝贝”,从不谈性爱的冰心到欲望写作的“新生代”女作家,非左即右,非此即彼。而新时期以来的女作家又大多是在文化废墟上开始艰难跋涉,文化底蕴不足,儒家文化对她们而言,更多的是被政治运动利用的工具。极“左”路线下,一方面是狠批特批儒家,另一方面却又把儒家“灭人欲”发挥到极致,这深刻的悖论使得当时的文学既无人伦温情可言,又扼杀了人的自然欲望,因此她们在承受儒家文化负面影响上比台港澳暨海外华文女作家更为深重。精神分析学认为,文艺是作家满足被压抑的欲望的曲折方式。这样,对以往僵化的政治文学形态的摒弃,对女性话语权的争夺:儒家文化传承下女性写作的双面效应,促使女作家们勇敢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压抑愈久、压迫愈重,反抗也愈烈,故而一旦开禁,即如洪水决堤,来势凶猛而锐不可当,对大陆女作家而言,她们不仅要颠覆父权制社会把女性身体物化及商品化的男性叙事,而且还要反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强权话语所造成的“无性别”意识。所以,对长期压抑的愤懑使她们在展示女性生命体验的时候,更多地与失落、痛楚、受伤、扭曲联系在一起,两性的对立与对抗、女性偏执的怨愤和锥心的痛感使得中国大陆女性写作在表层形式上显得并不和谐。
注释: 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2页。 参考文献: [1]黄建中.中西道德之异同.郁龙余编:中西文化异同论[M].三联书店,1989. [2]钟玉莲.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中国孔子基金会主编:儒学与廿一世纪(上)[M].华夏出版社,1995. [3]王永炳.儒学与廿一世纪的新加坡家庭价值观.中国孔子基金会主编:儒学与廿一世纪(上)[M].华夏出版社,1995. [4]席慕容.无边的回忆.我的家在高原上[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 [5]简烦.路在掌中.只缘身在此山中[M].九洲图书出版社,2000. [6]冰心.(关于女人>后记.冰心文集(第1卷)[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7]陈染.破开.危险的去处(陈染作品自选集?上)[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8]盛英.云破月来花弄影(澳门女性散文一瞥)[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1). [9]张晓风.爱情篇.从你美丽的流域.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10]林自语.林自等.九十年代女性小说四人谈[J].南方文坛,1997(2).11
由起名专家专业的命理起名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