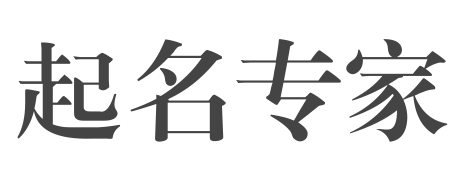南怀瑾老师:假仁假义的正当性必须由道
时间:作者:起名专家
南怀瑾老师:假仁假义的正当性必须由道
这假仁假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必然结果。
因为仁本身就是一种心灵的感受。绝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而仁这种东西的维护力量就只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是一种非常小的力量,根本抵不过各种各样利益的诱惑,所以仁这种东西实际上面临大是大非或者大的利益诱惑就完全不起作用,然后再配上儒家专用的春秋笔法,互相欺骗欺骗别人自我欺骗。那肯定会变成假仁假义。
例如曾国藩还有整个湘军的上层,中层,下层对江南实行三光屠杀,杀掉了一万万到两万万汉人,他们也觉得自己非常的仁义道德。理直气壮,没有任何的不适应。这就不能说是假仁假意了,这简直就是用仁的名义来进行反人类犯罪。
即使仅就伦理学而言,儒家也有严重失误。一种规范是否具有正当性,这是需要由道德价值去证明的,就是说,礼的正当性必须由道【客观规律】德【公平分配利益】去解释。可是儒家总是反过来以礼去定义道德,合乎礼的才被认为是道德的。礼与道德的地位颠倒是一个致命的伦理学错误,进而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政治错误,正如老子敏锐的发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13]。很显然,礼不能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因此不能把礼看作是无须价值辩护的规则。如果次序颠倒,规范被当成是对价值的解释,事情就乱了,人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偏好去规定各种各样的规范,这样就会有各种各样互相冲突的伦理,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说礼是“乱之首”的理由。
以下是引用文件:
尊尊原则就不是一个普遍必然的人情选择,比如说,尊强、尊智、尊能、尊贤甚至尊美或者干脆人人平等,都至少不弱于尊尊的吸引力和支持率。认真说来,尊尊是相比之下最缺乏理由的选择,无论是智慧、勇敢还是高尚品德甚至美貌,其本身就是人人希望自己能够具备的优越性,也是人类从事各种事情所需要的能力和条件,而人人平等普遍尊重了每个人的人格,这些都比尊尊更符合人们的需要。上下尊卑关系完全是特定伦理(礼)所定义的,并非人们的普遍意愿。尊尊所规定的等级制度和论资排辈秩序是一个老谋深算的统治策略,但其阴险效果从长期来看会造成社会的慢性衰竭。尊尊意味着:一个人即使愚蠢无德,只要熬成老者或者领导就将获得巨大利益;同时,一个人即使弱智卑鄙,只要惟命是从,阿谀奉承,那么他将从领导或长者那里获得发达的机会。尽管儒家也声称社会需要贤能,但尊尊原则的地位高过贤能原则,因此贤能原则总是在实践中被瓦解。
在一个价值观体系中,选择什么东西作为至高价值是需要无比谨慎的问题,因为当其它价值在与最高价值发生矛盾时,其它价值就必定被牺牲掉,因此,只有最高价值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一价值体系的元定理决定了,如果最高价值选择不当就会使整个价值体系失去正当性,即使这一体系包含了所有好的价值也无济于事。儒家价值体系在内容上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许多好的价值,但其最高价值的配置不当,其它好的价值再多也会被消解。尊尊原则就是最为不当的一个配置,它本身不是一种绝对价值,而且缺乏来自绝对价值(真善美之类)的支持,其唯一目的就是维护长老权贵的利益。亲亲原则虽然是正当配置,但又没有能够构成对尊尊原则的制约,反而有用人唯亲的不良作用,因此儒家价值体系的设计是非常可疑的。陈胜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就是对尊尊的反动,不过陈胜的理由也不是正当理由,它促进了与专制同样有害的暴民传统,而腐败统治和暴民作乱是对社会的双重伤害。尊尊原则最为深远的危害就是取消了政治合法性问题。按照周思想,政治合法性来自贤能德治而获得的民心,贤能德治是政治投资,是获得政治合法性所必需的成本。儒家在继承周思想时过分突出了尊尊原则并且使之绝对化,这样就等于暗中取消了政治合法性问题。显然,儒家并没有完全“从周”,而是半从周半背周,因此,儒家与“周家”不是一家。
推爱问题更是儒家的关键所在。亲亲是自明的(这是事实),但亲亲显然不够,还必须能够推爱及众,才能够构造出普遍有效的伦理。正如孟子总结的,儒家伦理无非“善推”而已[8],如果推不成,儒家就难以成立了。当以亲亲原则进行推爱,就形成了后来被费孝通描述为“同心圆”结构的伦理体系,所谓层层外推而达到爱众。推爱及众的严重困难是推爱推不出多远,恩义就非常稀薄了,最后完全消失在变得疏远的关系中,推不远所以推不成。这个困难的另一面是:天下有无数家,任意一家与另一家之间同样存在着与个人之间一样的矛盾和冲突。这说明亲亲模式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个充分的伦理基础,它对解决社会冲突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由家伦理推不出社会伦理,由爱亲人推不出爱他人,这是儒家的致命困难。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孟子构造了性善论(孔子对人性的估计并不乐观,后世儒家普遍认同的性善论是孟子制造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可以想象,假如人性本善,推爱他人就是可能的了(尽管仍然不必然),只要是可能的,礼治教化的成功率就会增大。其著名论证说人本性有恻隐之心等“四端”,好比人有“四体”一样是天经地义。这套论证的每一点都是错的:(1)四端中除了恻隐之心似乎属于自然人性(尚有待证明),而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都属于教化人性,把教化结果说成是自然本性,显然颠倒因果;而且(2)随便挑出几种善良之心去证明性善是无效的,因为性恶的证据恐怕远远多于性善,更糟的是,性恶之心几乎都比性善之心更有力量,最为显著的是自私之心无处不在,其动力之大,即使为了蝇头小利也足以利令智昏而草菅人命。现代科学的证据显然更有利于性恶论,趋利避害、自身安全、争夺生存条件和生存优势甚至侵犯性,都被证明是人性中最具决定性的天性。相比之下,恻隐之心等四端对行为并没有普遍影响力,都只在特定情景中才起作用,而且其力量非常有限,通常只够做出非常有限的善举(无非小恩小惠),而不可能超越保护自己利益和安全的私心。总之,自然人性善的力量远远小于自然人性恶的力量;(3)人间确实存在着一些义薄云天的事情,但也与孟子所列举的性善之心无关,恻隐之心太渺小,不可能超越自私的力量而成就义薄云天的壮举,因此,自我牺牲的动力必定来自文化所创造的某种强大的精神。一般地说,义薄云天的事情都源于高度精神化的壮丽宏大的感情或意识,比如伟大理想、真理的追求、宗教使命或者深刻的爱情,甚至无可抗拒的美也能够让人牺牲生命,这说明真正的爱和利他行为必定源于伟大的感情和思想,而不可能来自恻隐之心之类的小情小调。既然恻隐之心之类不可能导致人们做出足够大的利益让步和自我牺牲,就显然远远不足以解决社会冲突,那些小小的善良对于人间苦难来说几乎是万里之遥的杯水车薪;(4)孟子的类比论证法完全不伦不类,假如四端与四体是有效类比,那么既然人性实际上有许多“端”,是不是就应该说人有许多“体”?此类荒谬论证在任何地方都是无效的。儒家中思想最清楚的荀子就以严密得多的性恶论断然拒绝了孟子的性善论(但荀子却被后世忽视)。性善论不成立,使推爱工程彻底失去希望。
可以肯定,儒家伦理体系对于解释社会是不充分的,亲亲尊尊原则加上推爱原则还是不能有效地建立良好社会关系。一个充分有效的伦理体系到底需要多少个基本原则,这一点很难确定,也许可以有多种方案,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有效的伦理体系不管有哪些原则,其中必须至少包括一个能够解释任意一个人与陌生人关系的普遍原则,否则是说不通的,因为陌生人才是典型的他人,不能解释陌生人就等于不能解释他人。陌生人原则应该是任何一个充分有效的社会制度的第一原则,如果能够成功处理陌生人问题,其它关系就相对容易处理了。儒家主要解释了熟人关系,在陌生人问题上含糊其辞,只是幻想能够推爱。正如前面分析的,推爱方案既无力又牵强,实在不算“善推”。关于儒家思想局限性有一个辩解是,儒家的熟人伦理在古代是够用的,因为古代就是熟人社会。但这一解释是很不真实的,古代的熟人生活的确比例比较大,但陌生人无疑是普遍存在的(除非像老子想象的“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而且,不同的熟人共同体之间也相当于陌生人关系,比如一乡与另一乡的关系,一国与另一国的关系,如此等等,因此,陌生人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回避了陌生人问题的伦理或政治体系都是无效的。
当然,陌生人问题至今没有令人完全满意的解决。西方最负盛名的方案是契约论,它试图以公平为操作原则,以公正为理想,通过明确各人以及各政治主体的权利和利益而形成普遍合作关系。但是自私的人性将千方百计去利用制度的一切漏洞去背叛契约,造成“制度渗漏”现象,甚至破坏制度的公平操作乃至制度本身,因此契约仍然是不可靠的;更重要的是,契约背后是实力博弈,于是,契约要做到公平是可能的,但要做到公正就很困难了。周的天下体系包含了关于他者问题以及合作问题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但主要是关于国家级别的政治实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原则,还没有具体落实到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推进的,在此不论。至于儒家,由于没有构造关于陌生人的理论,因此儒家对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能力必定是非常有限的。
可以看出,儒家虽然付出很大努力,但并没有能够在理论上解决社会冲突问题。不过,理论缺陷有时候可以在实践中去弥补,但缺乏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实践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儒家礼教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为了让礼教充分发挥作用,于是礼教就在实践中获得不正常的膨胀,渗透到生活的每个方面。这样确实多少发挥了社会治理的作用,但这种礼教膨胀是病态的,后患无穷。礼作为一种分配和管理制度,当它被滥用而无穷扩张,它就将分配人们所感兴趣的一切东西,权力、权利、利益、义务、责任、荣誉、地位以及对待和被对待的方式,它将规定生活方方面面的价值观,甚至对话语和情感表达方式以及身体的使用方式进行管理。大概除了爱憎和声望无法分配之外,礼试图分配管理一切事情,礼既是管制一切的规范,又是解释一切的意识形态,这样礼教就把整个生活都政治化了,在这个意义上,假如礼治工程全面成功,伦理就真地变成了对政治问题的解决,但这样的解决方式是否可取,却是非常可疑的。
当生活几乎所有细节都被礼教以政治化的方式加以管制,甚至连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都被管制,这是非常可怕的生活。礼治与法治虽然都是管制方式,但法律仅仅是明确划分了自由的行为空间和不自由的行为空间。法律想告诉人们的是:如果希望避免惩罚,就只能选择在自由空间里去行为。与此不同,礼几乎不留自由空间,礼要告诉人们的是:如果想要得到任何利益,就必须按照礼的管制方式去行为,否则就只好放弃利益。表明上看,礼教不鼓励法律的强制和暴力惩罚,因此礼教似乎比法治温和,但礼教留给人们的是一种典型的伪自由,因为人们一旦选择了自由就等于放弃了生活所必需的利益,那样就无法生存了,因此只好自愿屈服,可见,礼教的本质是反自由。这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家们声泪俱下愤怒声讨残酷礼教的原因,礼教被认为除了“吃人”别无作为,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如此云云,虽是过度批判,但也显然击中了礼教的要害。
从《仪礼》看,周的礼治虽然烦琐,但没有形成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自由等基本自由的严格管制。而且,周的礼治主要是在“国”(城市与郊区)中实施,而在“野”(偏远地区或者无政府地区)则非常薄弱或甚至不存在,因此,不愿意受管制的人们仍然有条件逃逸在外。精神上和地理上的自由空间是保证政治活力的重要条件,只有当人们有地方可逃,有可能逃逸在控制之外,才能形成对一种政治的外部压力,这样才能迫使这种统治愿意成为好的统治,使得人们愿意接受这种统治以便分享其治下利益。一种好的政治将使人们发现,治下利益大于背叛的利益,于是人们将理性地选择政治合作。看来儒家不懂这一政治原理,因此错误地理解了礼治,以为只要增加礼治的强度和密度就能够控制社会,结果把原本具有积极文化意义的礼治变成了反自由的制度。礼治成为无孔不入的反自由的礼教应该是宋儒之后的事情。宋明儒家是典型的误国意识形态。
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式的复礼运动却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孔子奔波多国无功而归,理想破灭而几乎“乘桴浮于海”。春秋战国是礼崩乐坏的乱世,也是利益分配重新洗牌的难得机会,因此任何有实力的人都不可能放弃这一机会。一旦礼崩乐坏,就只能等到完成利益的重新分配才可能回到礼治。春秋战国时各国所需要的是能够成就霸业的策略而不是伦理学,所以法家、兵家和纵横家更受欢迎。在后来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里,儒家的治理价值才被重新发现而终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家以伦理去主导政治的伦理学转向其实是政治的慢性毒药,它会导致政治的慢性衰竭。当礼教被作为政治,它就不得不去对付那些它本来对付不了的问题,超负荷的过度膨胀迫使礼治败坏自身而变成反自由的制度。
即使在礼教衰竭之前,礼教的真实作用也是很可疑的。伦理或许能够对付小利益问题,却对付不了大利益问题;只能管住鸡毛蒜皮的事情,对大事则无能为力,人们在巨大利益面前就不再“有耻且格”了。权力或者巨大财富之类的东西足以改变命运,其力量远远大于伦理,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宫廷和官场无比险恶,而日常生活则相对安全,因为日常生活较少有值得拼命的利益。但即使是日常生活,伦理的作用也远远不如想象的那样大,正如吴思的《潜规则》一书所描写的中国古代真实生活,人们只要拥有哪怕很小的权力,也会用于谋取哪怕很小的利益而不惜伤害人命,如此等等[9]。更严重的是,礼教只尊重名分地位儒家思想的仁义,而不尊重人本身,于是无形中鼓励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损人不利己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喜欢伤害他人,因为伤害他人是一种快感。正因为伦理的力量远远小于利益的力量,因此,伦理在社会合作方面的贡献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大。老子看到了这一点,对伦理进行了尖刻的批评,但老子解决社会冲突的方案有一种令人绝望而且荒唐的深刻:使生活回归到极其简朴的水平,使社会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值得争夺的东西,没有可争的,所以才能不争。
其实孔子自己早就知道伦理规范是靠不住的。除了《论语》中的若干言论,《礼记》中有一篇传说属于孔子的言论特别表达了这一困境,这篇言论如此有趣,不妨大段引述如下(其中删节了一些意思重复的言论):
“子云:贫而好乐,富而好礼,众而以宁者,天下其几矣。《诗》云: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故制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子云:觞酒豆肉让而受恶,民犹犯齿;衽席之上让而坐下,民犹犯贵;朝廷之位让而就贱,民犹犯君。《诗》云: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子云: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慈;闺门之内南怀瑾老师:假仁假义的正当性必须由道,戏而不叹。君子以此坊民,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子云: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子云:敬则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废礼,不以美没礼。故食礼,主人亲馈,则客祭,主人不亲馈,则客不祭。故君子苟无礼,虽美不食焉。《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子云:升自客阶,受吊于宾位,教民追孝也。未没丧不称君,示民不争也。故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儒家思想的仁义,子犹有弑其父者。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长,示民不贰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儒家思想的仁义,莫敢为主焉。故君适其臣,升自阼阶,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示民不敢专也。以此坊民,民犹忘其亲而贰其君。子云:礼之先币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先财而后礼,则民利;无辞而行情,则民争。故君子于有馈者,弗能见则不视其馈。以此坊民,民犹贵禄而贱行。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故君子仕则不稼,田则不渔,食时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坊民,民犹忘义而争利,以亡其身。子云: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此坊民,民犹有自献其身。子云: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以此坊民,民犹以色厚于德”[10]。
可见,无论大利小利,人们都经不起考验。当然,孔子只是说,总有些人见利忘义,并没有说所有人都见利忘义,因此孔子对复礼仍然怀有顽强的企望。唯一的渺茫希望就在于儒家力推的“榜样模式” [11],就是克己修身,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最后达到普遍的见贤思齐。儒家以为光辉的道德形象必定具有吸引力,于是精心打造各种正面形象,从圣人、仁者、善人到君子之类。看来儒家并不理解榜样问题的要害。“榜样”到底被编造成什么模样,这是相对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道德“榜样”是否同时是社会成功的“榜样”,就是说,道德上的榜样必须与利益上的成功榜样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榜样”就失去魅力,因为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利益上的成功,而不是做一个在形象很光辉但在利益上很失败的人。能够把功名利禄看成浮云粪土的伟人高人毕竟凤毛麟角,只能是人们景仰和颂扬的对象,而不可能成为人们的模仿对象,因此在社会解释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上面所引述的“坊记”篇看出,孔子也知道榜样的力量决非无穷。法家更是发现了榜样的教化作用是可疑的,商鞅指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2]。仁者能够做到的仅仅是自己成为仁者,而不可能把他人变成仁者。“不能使人仁”与“推爱不远”是儒家的并列的两大局限性。榜样和推爱都是有益的事情,永远值得称颂,但无法克服社会的各种难题,因为榜样和推爱都只是或然有效而非必然有效的办法,所以是不可靠的治理。儒家的失误从根本上说是思想方法论的失误。
可见,无论大利小利,人们都经不起考验。当然,孔子只是说,总有些人见利忘义,并没有说所有人都见利忘义,因此孔子对复礼仍然怀有顽强的企望。唯一的渺茫希望就在于儒家力推的“榜样模式” [11],就是克己修身,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最后达到普遍的见贤思齐。儒家以为光辉的道德形象必定具有吸引力,于是精心打造各种正面形象,从圣人、仁者、善人到君子之类。看来儒家并不理解榜样问题的要害。“榜样”到底被编造成什么模样,这是相对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道德“榜样”是否同时是社会成功的“榜样”,就是说,道德上的榜样必须与利益上的成功榜样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榜样”就失去魅力,因为人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利益上的成功,而不是做一个在形象很光辉但在利益上很失败的人。能够把功名利禄看成浮云粪土的伟人高人毕竟凤毛麟角,只能是人们景仰和颂扬的对象,而不可能成为人们的模仿对象,因此在社会解释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上面所引述的“坊记”篇看出,孔子也知道榜样的力量决非无穷。法家更是发现了榜样的教化作用是可疑的,商鞅指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2]。仁者能够做到的仅仅是自己成为仁者,而不可能把他人变成仁者。“不能使人仁”与“推爱不远”是儒家的并列的两大局限性。榜样和推爱都是有益的事情,永远值得称颂,但无法克服社会的各种难题,因为榜样和推爱都只是或然有效而非必然有效的办法,所以是不可靠的治理。儒家的失误从根本上说是思想方法论的失误。
“榜样”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制度问题:如果一个制度不能在德与利之间建立一致性,就必定是个失败社会。儒家社会所以是失败的,原因在于,社会的制度安排从来都没有能够使有德之人更多受益,甚至反而损害有德之人的利益。亲亲尊尊与任贤使能是互相矛盾的,因为亲亲尊尊的结果是用人唯亲和论资排辈,而一旦不能做到任贤使能,就必定在客观事实上使道德榜样失去号召力而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因此儒家虽有伦理理想,却事与愿违。儒家思想的自相矛盾是由儒家不懂政治造成的,它在继承周思想时把政治和伦理混为一谈,因此造成了亲亲尊尊与任贤之间的冲突。在周思想中,政治与伦理是有分别的,周的分封优先了亲亲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人会把既得利益拱手相让,但周在政治治理上强调的是德治,以无私治亲、任贤使能、养民利民为首要任务,以公正的长期治理原则去弥补起始的偏私分配,这显示出周公们清楚的政治意识。亲亲与任贤本来没有矛盾,亲亲原则的有效领域是生活关系,而任贤的有效领域是政治管理。儒家把伦理与政治混为一谈,也就平白制造了自相矛盾的思想。德与利无法统一,这对于儒家是个釜底抽薪的打击。一种意识形态或主流话语高扬什么价值,这不能说明问题,重要的是实际生效的社会奖励,即做什么样的事情和怎样做事情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收益。假如主流话语认为道德光荣而缺德可耻,可是在实践中缺德更能获利,那么等于证明了缺德才是光荣的,而道德榜样变成了一个摆设。所以,政治的关键问题是,是否存在某种制度安排,使得人们好德胜过好利?答案只能是:除非建立一种制度使得有德是获利的必要条件,否则善就没有诱惑力。
即使仅就伦理学而言,儒家也有严重失误。一种规范是否具有正当性,这是需要由道德价值去证明的,就是说,礼的正当性必须由道德去解释。可是儒家总是反过来以礼去定义道德,合乎礼的才被认为是道德的。礼与道德的地位颠倒是一个致命的伦理学错误,进而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政治错误,正如老子敏锐的发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13]。很显然,礼不能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因此不能把礼看作是无须价值辩护的规则。如果次序颠倒,规范被当成是对价值的解释,事情就乱了,人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偏好去规定各种各样的规范,这样就会有各种各样互相冲突的伦理,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说礼是“乱之首”的理由。
儒家一心希望建立良好社会,但不得其法。伦理不可能解决政治问题,礼治支撑不起政治,克己也不可能复礼。虽然任何一种政治都必须在某些方面限制自由,否则社会不可能有秩序,但是如果全面反自由,就非常危险了。儒家礼教在限制重大罪恶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却不遗余力地去管制那些与道德基本无关的生活风格和细节,坏事没有管住,却限制了好事。管制不该管的事情就是规范的膨胀。尤其是宋儒之后南怀瑾老师:假仁假义的正当性必须由道,礼教压制了与众不同的人和创造性思想,抑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使生活充满虚伪、圆滑、懦弱、阴暗、谄媚、人心叵测、人言可畏的气氛。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主流秩序对其治下的阴暗病弱中国恐怕难逃其责。这一事实不是儒家所能够辩解的。社会学可以证明,主流话语和宣传不能表明社会真实,民谣民谚才是社会真实的表达,而民谚民谣恰恰表明了儒家社会是一个以不信任为主要风格的社会[14]。
由起名专家专业的命理起名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