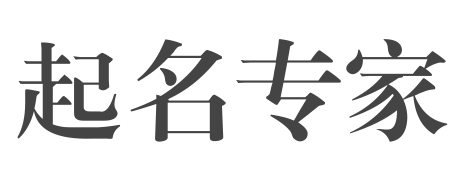廖晓炜:多维自我观的视角重新解读儒家的自我
时间:作者:起名专家
廖晓炜:多维自我观的视角重新解读儒家的自我
廖晓炜,哲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先秦儒学、明清儒学、中国近现代哲学。
摘要:如何理解儒家的自我观,是一颇具争议的课题。过往的研究或从关系、角色的角度理解儒家的“自我”,强调其与近代自主性个体观念之间的差别;或将儒家的自我界定为先验的主体,并由之肯定儒家自我的自主性与个体性。本文则尝试从多维自我观的视角重新解读儒家的自我观。以孟子哲学为例,孟子的自我观念,其实包含反思性、身体性、关系性及宗教性,也即心性、形气、人伦与天道四个维度。就现实的层面而言,四个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但就应然的层面来看,四者共同构成一“整全的自我”。以之为基础,我们可以对儒家伦理学的定位问题,略作回应。
关键词:《孟子》;多维自我观;儒家伦理学
一、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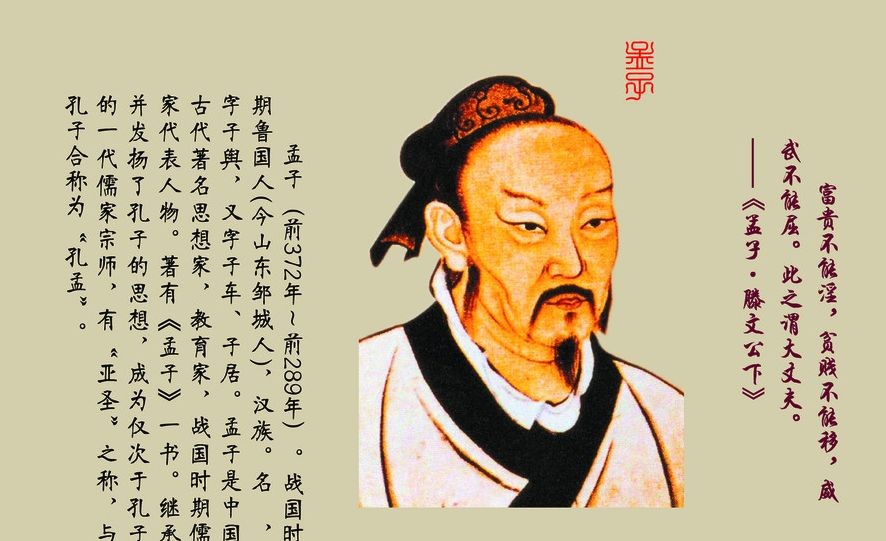
如何理解儒家的自我观,可说是思考儒家伦理学之理论性格的基础和前提。学界在儒家伦理学定位问题上的争议,背后隐含一更为基本的理论分歧,即是对儒家自我观念的不同解读。如何信全以孟子持义务论伦理学的立场,孟子的自我乃一康德式的先验主体( );【1】以德行伦理学诠释儒家伦理学的学者,则多强调儒家的自我乃一关系性的自我( self);【2】安乐哲等人则将儒家伦理学界定为角色伦理学(role ),认为儒家并不预设个体自我的存在,所谓的自我不过是各种关系与角色的总和,在诸多关系之动态叙事的背后,并没有一个承载这些关系或角色的个体自我;【3】也有学者强调儒家伦理学是一种示范伦理学,作为其基础的关系性自我,应该更准确地界定为“系谱学的自我”( self)。【4】因此,本文将聚焦于《孟子》,透过具体的文本分析,以澄清《孟子》中“自我”的理论意涵,并就儒家伦理学的定位问题,略作回应。
就问题意识而言,本文试图客观而完整地揭示,孟子哲学中作为特定个体之人()的“自我理解”的诸构成要素是什么?相互之间有何内在关联?这颇类于 、John 等人所提倡的“多维的自我观”或“自我的整合理论”。【5】本文认为,孟子所理解的“自我”大体包含心性、形气【6】、人伦、天道四个维度,前三者约略相当于 所谓的反思性的、关系性的以及身体性的这三个维度。【7】“天道”则指向“自我”的宗教或精神性维度( or )。
二、心性:儒家式的道德主体
诚如信广来所指出的,儒学中包含一以自我反思的方式与自身相关联的自我观念,这一自我反思的能力通常被归之于“心”。【8】在孟子这里,该反思性的能力即体现为心官之“思”,如“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告子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告子上》)可见,吾人以何种方式对待“身”、如何理解自“己”、是否能把握自身所本具的“仁义礼智”,其关键都在心之思与不思。
此外,由“志”这一观念,乃可见出,孟子哲学中的“自我”乃一具有“自主性”的行动主体。基本上,对孟子而言,“志”乃心官之能(),其可选择并决定我们的具体行为乃至整体人生的方向。此所以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公孙丑上》),并强调“立志”(《孟子·万章下》)、“尚志”(《尽心上》)以及“专心致志”(《告子上》)等于自我修养上的重要性。Rina Marie Camus对此有极为详细的阐释,本文不赘。【9】
突出心或自我的反思性与自主性,可说是传统儒学的基本共识。但就道德哲学的角度而言,孟子所理解的“心”或“道德主体”,有其较为特殊的性格,这是本节要着重阐述的。在孟子哲学中,作为道德主体的“心”,乃道德行为所以可能的条件。具体言之,道德主体的这一性格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1、心具足为善的能力,孟子以“才”与“良能”等观念说之;【10】2、心本身即是为善之动机的来源,此即心之情感面;3、心自身即可决定具普遍性之道德法则或曰道德行动的方向。
由孟子与齐宣王有关“不忍牛之觳觫”与“保民而王”两者间之关系的讨论,我们不难理解上述第一点意涵。在孟子看来,齐宣王能因不忍牛之觳觫,而“以羊易牛”,正表明齐宣王具有“保民而王”的充足能力,此孟子所以说:“是心足以王矣”。表面来看,舍牛而不杀易,保民而王似乎更难。然孟子却认为:“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梁惠王上》)孟子的意思非常清楚,相较于对牛的不忍,心更易于感受到作为同类的百姓的困苦。所谓保民而王,不过是顺此心不忍百姓处于困苦之中的内在要求而为,正如不忍牛之觳觫,进而通过以羊易牛的方式,舍牛而不杀。人心完全具备做到这两者的能力。必须说明的是,如何解决不废衅钟与舍牛不杀之间的矛盾,以及以何种标准保障百姓的生活,自然会受到特定情境与条件的制约,非人力所能完全决定。但按照善的要求去为,在孟子看来,这能力乃是人心本自具足的。【11】有学者认为,孟子的这一想法,正合乎康德哲学“应当蕴涵能够”之义。【12】“能”而“不为”的区分,即意在突出这一点。事实上,这也是孟子言性善所特别强点的一点。当然具足为善的能力,并不表示人于现实中必然会为善。在孟子看来,人之不为善乃至为不善,只是“不为”,而非为善的能力存在任何欠缺,有如人之所以看不到“舆薪”,并非没有看的能力,只是这能力未被使用而已。
孟子答公都子性善之问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筭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告子上》)“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中的“可以”正指“能而不为”的“能”;“才”则指上文所谓“人之足够为善的能力”,【13】孟子亦以“良能”说之。孟子在另一处言及“四端之心”时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公孙丑上》)赵岐注曰:“自谓不能为善,自贼害其性,使不为善也。”【14】可见,对孟子而言,“性善”的核心意涵在于:人性先天具有充足的为善的能力(),【15】该能力亦即作为道德主体的“四端之心”的“才”或“良能”。
不过,具足为善的能力,并不表示人于现实中必然会为善,尚须特定的动机()作为行善的动力。在孟子看来,作为道德主体的“心”,有其情感性的面向,换言之,心具有某种特殊的感受能力。以孟子最为著名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于”的思想实验为例,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的一刹那,顿生“怵惕恻隐”之心,换言之,“心”内在地生起一种“不忍”、“不安”之感。此时,唯有通过施以援手,以使孺子免于危难,内心的不忍、不安之感,方可免除;进而,内心更可获得一种满足感。这也即孟子所谓“理义之悦我心”(《告子上》)。可见,“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心生怵惕恻隐之感的同时,内心亦生起应援救孺子的内在要求。因此,就道德实践而言,心的上述感受能力,正是道德行动之动机的来源。换言之,心的情感面或其感受能力,也可说是“必然向外表现的一种能力”,以传统儒学的话来讲,即所谓“性分的不容已”。【16】事实上,孟子言“养心之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如何保证心之上述感受能力的敏感性不会受到伤害。孟子从“仁术”的角度对“君子远庖厨”的正面肯定,也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得到最为合理的解释。
正是基于孟子所言之心的上述性格,牟宗三对孟子哲学中的“才”与“(良)能”有一较为特别的解读:“孟子说此‘才’字犹不只是静态的质地义,且有动态的‘能’义(活动义)。但此‘能’又不是一般意义的‘才能’之能。它即是‘性之能’。故此才字,其实义是动静合一的。……‘能’是紧指性体之实自身之自然而不容已地向善为善之能言,即恻隐等心之具体呈现、沛然莫之能御也。”【17】牟宗三的表述略显抽象,不熟悉孟子哲学的人,不易把握其真实涵义。若以前文所述为参照,则不能不说,牟宗三以“动静合一”说才、强调“能”的“活动义”,很好地揭示了孟子哲学中“心”本具必然要求自我实现的特殊能力这层意思,而其正是道德行动之动机的根源所在。
需要稍作说明的是,以德行伦理学为视角诠释孟子的学者,多倾向于将孟子哲学中之“心”的情感面或感受能力,理解为萌芽状态的道德倾向或道德感( moral or ),【18】经由后天之习惯与实践的型塑与培养,这些萌芽状态的道德感可发展为相对稳定、成熟的情感反应能力。这类解读虽与当代道德心理学的相关讨论颇为契合,但与孟子的本意存在相当的距离。【19】任满悦( Im)认为,上述解读是否符合孟子的本意,乃是十分可疑的;对孟子而言,人的道德发展无须习惯或实践的强制作用,而仅需最低限度的条件作为保障:如物质条件的满足、稳定的社会条件等。【20】任满悦对《孟子》原文的分析极为细致、客观,颇具说服力。事实上,感受能力及为善的行动能力,均只是心的不同面向。而孟子言心,尤为强调以下几点:1、普遍性:其为人所普遍共有;2、心与感性官能之间的区别,亦即“大体”“小体”之辨;3、先天性与自足性,所谓“此天之所与我者”。正基于此,一些学者强调孟子所言之“心”,非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心,而是先验的或超越的道德主体,如牟宗三曰:“孟子所说的‘心’是 and and moral,不是泛泛说的心理学的心。道德的而又是本心,所以,这个‘心’是(超越的)。‘超越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超越于经验以上的,不能由经验而得到,而又反过来支配经验,指导经验,指导我们的感性。照康德的使用就是如此。”【21】易言之,心与感性官能之间具有一种非化约性的关系。
此外,以德行伦理学为参照诠释孟子的学者,往往也强调儒学真正关注的是德行的培养,而非抽象的道德法则。不过,诚如有学者所已指出的,古典儒家所谓仁义礼智等诸德目概念,往往兼指德行、德性、原则等,【22】这可说是一较为客观公允的论断。顺此,我们即可进而说明孟子所言之道德主体的第三项特征:道德法则由心自身所决定。如果说仁义礼智等德目概念,亦指原则的话,那么作为行为之规范的原则是如何确立的呢?孟子以为道德原则与心之间,有其必然性的关系:“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告子上》)。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这种“同一性”关系呢?同样以“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思想实验为例,见孺子将入于井,顿生怵惕恻隐之心,若无其它因素的阻隔,心之怵惕恻隐必发而为援救孺子的行为,此行为本身即可说之为“仁”,当然此时若“见死不求”,则为“不仁”。在此情境下,应援救孺子,乃一具有必然性的行为要求,换言之,仁乃一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规范。此行为要求并非思虑考量之后的结果,因“乍见”正表示“不容思虑”。可见,恻隐之心的呈露,即表现为“应援救孺子”这一具有普遍性的行为要求。换言之,在此情境下,行为之方向乃由心自身所提供。【23】是以,有学者认为:“依孟子,‘道德律则’不外就是‘普遍化的情感’。”【24】因道德律则必具普遍性,因此作为其基础的心或道德主体,也只能是超越的()。
当然,如此定位孟子所言之“心”或道德主体,易使人误以为孟子哲学中的自我与近代西方哲学所强调的自主性的自我并无多大差别。因此,我们更须说明“心”与形气、人伦及天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更为完整地把握“自我”在孟子哲学中的图像。
三、心性与形气、人伦及天道
在孟子哲学中廖晓炜:多维自我观的视角重新解读儒家的自我,心性与身体或形气之间的关系,【25】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看。就现实的层面而言,形气会限制、障蔽心性的表现,此所以孟子有大体(心之官)、小体(耳目之官)之辨,并强调“大体”于道德实践上的优先性,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告子上》)。此外,由孟子“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公孙丑上》)之说,亦可见出,心性与形气之间所可能存在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孟子主张某种形上学意义上的“身心二元论”。由《孟子》中“身”与“体”这两个观念之涵义的差别,不难见出这一点。
除“大体”“小体”之别外廖晓炜:多维自我观的视角重新解读儒家的自我,孟子言及“体”者还有:“四体”、“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可见,今日所谓的“身体”,在《孟子》儒家哲学核心概念,皆以“体”说之,也即“小体”。“心”,亦可以“体”言,不过是与“小体”有别的“大体”。“身”则是描述有别于他人之“自我”的一个特殊观念,其所指涉的是“我”的整个的生命存在,或曰大体与小体的统一体。由《孟子》中的以下表述,不难理解这一点:“穷则独善其身”(《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儒家哲学核心概念,乐莫大焉”(《尽心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等等。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孟子所特别用到的“修身”一词,当指通过个人的努力以实现整个生命的自我转化。循此,亦可见出,在孟子哲学中,“身体”乃“自我”所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
从一积极的层面而言,身体乃是心或道德主体表现自身、成就善行的载体,或者说,心所发动之善行,最终须通过身体来完成。从应然的角度来看,身体与心之间,可以达至交融合一的状态:“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这也是“修身”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人之仪容周旋无不是根于心之仁义礼智之体现。【26】这与《大学》“德润身”之说所指相同。
除此而外,由孟子“养气”说,还可见出,透过工夫修养,感性生命还可发挥助成吾人为善之积极作用。孟子解释“何谓浩然之气”时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公孙丑上》)由“知言养气”章的整体脉络,我们知道:“养浩然之气”乃孟子培养勇德,进而达至“不动心”境界的方法。那么“养气”与勇德之间有何关系呢?事实上,感性生命原本就有很强大的力量,所谓“血气之勇”或“匹夫之勇”,北宫黝之勇,即属此类。不过,感性生命的力量,乃是盲目无定准的。在孟子看来,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亦即集义的工夫,使其理性化。如此,感性生命所充之“气”即转化而为“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与此同时,感性生命所本有的力量,也就转变为助成人去为善的正面力量。在这意义上,感性生命或形气亦可与心达至合一的状态,成为人之为善的重要力量。

综上可见,就应然的层面而言,心与形气亦即感性生命之间可达至交融合一的状态,但就实然的层面而言,心与形气之间具有不可化约的关系。
再看心性与人伦之间的关系。“人伦”乃儒家最为基础性的一个观念,历来的儒者多以之为人之所以人为的构成性要素。孟子曾明确表达这层意思:“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离娄上》);“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同时,也只有基于人伦关系中的道德实践,人之成就理想人格,才有可能,此即孟子所谓“去人伦,无君子”(《告子下》)、“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就此而言,孟子所理解的“自我”必含关系性的维度,人只有在关系中才能成其为人。换言之,自我乃是人际关系的中心而非孤立的个人。【27】但这是否意味着,前文将源自人性的心理解为超越的道德主体,即与这里所强调的自我的关系性维度相冲突呢?【28】孟子哲学中的心性也因之只能是彻底境遇化、关系化和随机的吗?【29】这即涉及人伦在孟子哲学中的地位及其与心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借孟子对杨墨的批评来加以说明。
孟子批评墨子的兼爱,曰:“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滕文公下》),其与墨者夷之论辩时亦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滕文公上》)可见,孟子对墨家最根本的批评,就在于其忽视“人伦”的重要性。就孟子哲学而言,人伦方使得人成为一具体而真实的人(),抽象的或脱离人伦关系之外的孤立的个体,并不能称之为人。因此,道德实践上,这些人伦关系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也就是说,人所处的各种人伦关系,乃是道德实践得以展开的具体脉络。以“爱”为例,事实上,并无抽象的爱,爱一定是具体的,换言之,爱会因对象与我之关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这样的爱才是真实而具体的。“兼爱”对孟子而言,只是一抽象的原则,如不考虑人伦关系这一具体化原则,实践上,很容易让人陷入窘境。就此而言,为善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相对于主体”的(agent-)。【30】但这也不意味着,这些人伦关系所蕴含的行为规范,完全是外在于人的。由孟子对告子与杨朱的批评不难理解这一点。
孟子之所以批评告子的“义外”说,其中的一项考量是,如果道德规范只是外在的、习俗性的规定,人只能被迫按照规范的要求去行动,那么现实上,没有人真的愿意去为善。此所以孟子回应告子“杞柳杯棬”之喻时曰:“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欤?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告子上》)换言之,义外说理论上蕴含仁义与人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现实上,则可能导致人因捍卫人性而否弃仁义的局面。杨朱之所以倡“为我”之论,主张“拔一毛利天下儒家哲学核心概念,不为也”(《尽心上》),就是因为仁义这些习俗性的“身外之物”会对人的自然天性或生命构成束缚乃至伤害。《庄子》中也不乏类似的说法:“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骈拇》)可见,告子的义外说距离杨朱的为我论,仅一步之遥。因此,对孟子而言,回应杨朱之论的最有力的方式,即是澄清人性与仁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这即是上文所已说明的,孟子以源自人性的道德主体或心作为一切善的最终依据。人伦规范即是道德主体或心在诸关系脉络中的具体表达。可见,孟子以超越的道德主体来说明善的可能性条件,与强调人伦乃人之为人的构成性因素之间,并无任何理论上的冲突。人伦关系乃道德主体表现自身之具体的场域。人伦规范之所以具有合理性,正在于其植根于人性。是以有学者认为,儒家重视人伦、关系,并不表示儒家没有“主体性”的概念,儒家的“个人”与“主体”意义恰恰是在群体脉络中呈现的。【31】就孟子哲学而言,这一说法无疑是非常精准的。
最后再略述心性与天道之间的关系。孟子之所以突出对天道的关注,并非对原始宗教的直接继承,也非出于对形上世界之认知的兴趣。根本上来讲,天道之所以重要,在于人于道德实践中,不得不面对自身的有限性、也即命限的问题。此所以孟子论及心性与天道的关系时,亦涉及“命”这一观念:“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依孟子之见,人是否为善,完全由个人自主决定,所谓“求在我者也”;但主观的道德努力并不必然会促成一个真正正义的世界的出现,因这是“得之有命”的,根本不在人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是以孔子也不免有“道之不行”的感慨,而《孟子》终篇亦有“无有乎尔”之叹。就个人的层面来看,德福不一致的情况,更是常态。那么,该如何面对“命”的限制呢?孟子的回应是:“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或“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尽心下》)。问题是,“修身”、“行法”都只是主观上的道德努力,其所等待的仍只是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已?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我们在穷尽道德的一切努力之后,却发现我们仍无法不处在一个遭忧受苦、充满不正义的世界,这时我们就难免会面临到生命的努力终归枉然的虚无主义危机。面对这种生命意义的虚无处,‘我为何要行道德?’的强烈质疑将挥之不去。”此时,唯有宗教意识方能说明并支持为何遵行道德是一件有意义的行动。【32】
循此,我们即不难理解上引孟子论及心性与天道之关系的那段表述的思想意涵。“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指涉的即是“修身”。“修身”之所以能有效地回应命限的挑战,就在于透过心性上的工夫,可以进一步达至对天道的肯认。换言之,面对现实境遇的各种挑战,吾人仍能坚持道德理想的动力,其实是来自于某种宗教性的力量,亦即对天道的“诚信”。否则孔孟所谓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成不可解。宋明儒学以及不少当代学者,即顺此阐发孟子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当然,如何更为具体的从理论上阐明心性与天道之间的合一关系,仍是颇具挑战性的工作。不过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孟子所理解的道德主体或心性观念,实包含一宗教性的维度,或曰精神性的维度。在特定条件下,宗教意识乃是保证道德主体不至于自我坍塌的终极依据。因此,心性与天道之间的“合一”,似不应理解为“同一”,换言之,宗教意识与道德意识之间具有某种非化约性的关系;【33】同时,天道也不可完全外在化为人格神,否则,将与孟子对道德主体之自主性的强调构成理论上的冲突。

综上所述,孟子哲学中“自我”涉及心性、形气、人伦与天道四个维度,就实然的角度而言以心性为本的具有反思性、自主性的道德主体与形气、人伦及天道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不过就应然的层面或理想人格的层面来看,自我可说是由这四维度所构成的统一体。就此而言,孟子所构想的乃是一“整全的自我”。
四、结 语
最后,我们再从自我观的角度,对儒家伦理学的定位问题略作回应,以结束本文。对于安乐哲、罗思文而言,儒家根本无法按西方主流的伦理学思考来加以界定,因后者——不论是规则伦理学如义务论伦理学及功利主义伦理学,抑或是德行伦理学,均从根本上预设了带有本质倾向的自我或原子式的孤立个体,但对儒家而言,除了角色与身份之外,再无更为实质性的自我的存在,行为规范的标准不在于抽象的原则或德性,其完全由角色行为本身所决定。因此儒家伦理学其实是一种“角色伦理学”。【34】但就前文的分析不难见出,至少就孟子哲学而言,儒家固然突出关系、角色的重要性,但并未消解自我的自主性与个体性。就此而言,以“角色伦理学”界定儒家伦理学,其实是基于对儒家“自我”的片面认识。
就“心性”而言,孟子哲学中确实包含一先验的道德主体,并强调道德法则由道德主体自身所决定,此所以当代一些学者倾向于将孟子乃至儒家伦理学界定为“自律伦理学”。不过儒家同样也包含一套丰富的德行论,孟子哲学自不例外。这或许意味着德行伦理学与规则伦理学——就孟子哲学而言,至少德行伦理学与义务论伦理学——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35】劳思光先生即明确指出,一个完整的道德哲学理论,既要说明具体的、道德上的“好”(good)是什么,也应解释判断“好”之为“好”的形式原则如何确立,换言之,道德哲学对于德行伦理学及规则伦理学所面临的核心问题,都要有所答复。事实上,儒家伦理学正包含这两方面内容。【36】
本质而言,儒家哲学的核心关切在于,如何透过真实的自我理解以成就理想的人格。由于自我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儒家哲学蕴涵不同方面的伦理学意义,也非不可理解之事。此所以劳思光先生在肯定规则伦理学与德行伦理学之相容性的同时,指出:“儒学亦不是完全忽视道德生活之形式条件;不过儒学以成德之实践工夫为核心,因之对所谓‘Rule’及‘’之问题均收入工夫论中处理,与康德之思辨取向不同。只就‘ ’来看儒学也不能掌握儒学之真正特性。”【37】
因此,以当代西方伦理学的相关争议为背景,来观照儒家哲学,自有可以深度掘发儒学思想意涵的重要意义,不过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如何避免受这些争议的牵引,而陷入非此即彼的争论当中,反而错失儒学自身的本质与特色。
由起名专家专业的命理起名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