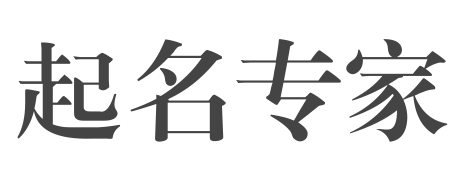黄玉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图)
时间:作者:起名专家
黄玉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图)

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
黄玉顺
摘要
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解构本体论”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然而,本体论恰恰是“哲学”的核心。本体论的必要性在于:人类关于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所有观念必定是一个有序的层级性的整体,它必定有一个塔尖,此即所谓“本体”;否则,人类的观念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因此,生活儒学的态度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为此,必须追溯到“前本体”即“前存在者”的存在或生活,即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因此,生活儒学建构了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进而建构了指向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
关键词:生活儒学;本体;超越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黄玉顺(1957—),男,四川成都人儒家是哲学还是伦理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儒家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
伴随着宗教的式微、科学的兴盛,“解构本体论”乃成为强大的哲学思潮。称之为“哲学思潮”,其实是吊诡的,犹如“被剜去了心脏的人”,因为哲学的核心恰恰是本体论()。所以,海德格尔( )宣告“哲学的终结”儒家是哲学还是伦理学,而试图以“思”(/)来取代;然而同样吊诡的是,这种非哲学的“思”却仍然被人们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不仅表明了哲学本身强烈的求生渴望,还暗示着整个人类观念系统实在无法割舍自己的心脏。笔者建构的“生活儒学”,也一直在回应这个问题,其主要看法是:必须解构旧的本体论,然而同时必须建构新的本体论;问题在于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本体论,以及怎样来建构这种本体论。
一、本体论何以必要
尽管众所周知,“本体论”这个术语直到1613年才由德国哲学家戈科列尼乌斯( )首次使用;但是,作为哲学理论事实的本体论,却是与整个哲学史相始终的,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米利都学派( )的泰勒斯()关于万物的“本原”(Arche旧译“始基”)的探讨,在中国可以追溯到老子和孔子之前即已存在的关于“天”或“道”的探讨。
这里所谓“本体论何以必要”,是针对人类的观念系统的整体而言的,即对于人的观念来说,本体论为什么是不可或缺的? 显然,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确定“本体论”的概念:本体论是什么? 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现成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从五花八门的说法中特别是从实际出现的哲学本体论的诸多历史形态中寻绎共性,加以归纳。
众所周知,“本体论”这个词语是由“ont”与后缀“-ology”两个部分组成的。“ology”意为“学科”“学”“论”;“ont”指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源自古希腊语εναι(being),意为“存在”。但是,海德格尔已经指出,哲学向来就已“遗忘存在”,即传统本体论的研究对象实际上并非“存在”,而是“存在者”,即中国哲学所谓“物”。由此看来,本体论就是一种关于存在者的理论。但如果仅仅这样讲,那还是并不充分的,因为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之处,在于哲学的对象不是某个“存在者领域”,而是全部“存在者整体”,中国哲学谓之“万物”。这就是说,本体论乃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理论,而呈现为所有观念的一个系统整体。
显然,这里的关键在于“本体”()的概念。从哲学史来看,“本体”有过两种含义:先是指宇宙论()意义上的万物的“本原”(Arche),中国哲学谓之“本末”之“本”(根株),强调的是“在万物之前”;后来是指狭义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者整体的“本质”(),略对应于中国哲学“体用”之“体”(实体、实质),强调的是“在万物之中”。两者其实可以统一起来,即如果将万物——众多相对的存在者都视为现象,那么,作为万物的终极本原的那个唯一绝对的存在者就是本质,这也就是万物的本体。这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拯救现象”的运动,即“人们出于对于变动不居的诸多现象的忧虑,试图在现象背后去找出某种唯一的永恒不变的本质或本体,由此而形成了‘本质与现象’‘形上—形下’等一般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因此,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所思考的往往都是某种永恒不变的实体。直到黑格尔的辩证法,尽管强调‘变’,但其终极根据恰恰是那个永恒不变的‘绝对观念’,即《逻辑学》的第一范畴‘纯有’”。所以,所谓本体,就是生成并且支撑所有存在者的那个终极存在者。
这样一来,实际上就已经显示了本体论的必要性:如果说,人类关于所有存在者之存在的所有观念必定是一个有序的系统(),而且这个系统必定呈现为一个金字塔结构的具有层级性的整体,那么,它必定有一个塔尖,此即所谓“本体”;否则,人类的观念就不成其为一个有序的系统,而只是一片混沌、混乱。这种“本体—万物”或“本体—现象”或“形上—形下”的关系,即“一”与“多”的关系,西方哲学谓之“奠基”,其实中国哲学的概念更为形象,叫作“立极”,即建房时的“上梁”:“极,栋也”;“极者,谓屋至高之处”。本体就是人类观念系统之中的那个“至高之处”,即“极”;建构本体论,就是“立极”,例如《周易》哲学的“易有太极”。
蒯因( Van Orman Quine)所谓“本体论承诺”(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笔者讲过:
形而上学之所以是必然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人类思想观念之构造的一种内在的逻辑承诺:对任何一个存在者领域之存在、甚至对任何个别存在者之存在的承诺,都已蕴涵着对存在者整体之存在的承诺。当我们说“a是B”或者“A 是B”的时候(小写字母表示个体,大写字母表示一个集合、种类),对a或A 的存在承诺已经蕴涵了对B的存在承诺;如此递进下去,我们最终必然走向对一个终极X 的承诺,这个X 就是存在者整体,亦即本体或上帝之类的形而上者。这一点最典型地体现在定义的规则中:定义始终意味着我们必须为这个被定义概念找到一个上位概念——比被定义概念外延更大的概念;如此递进下去,我们最终会找到一个不可定义的最高概念,这就是形而上者的观念。例如,从“某某是……的人”“人是……的动物”“动物是……的生物”一直到“……是造物”就是这样的递进序列。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用唯一绝对的存在者来说明众多相对的存在者何以可能;而任何一个陈述,最终都指向了形而上学。
这里所谈的“形而上学”,就是指的本体论。所以也就毫不奇怪:那些致力于解构本体论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们的言说本身,其实都蕴含着某种本体论承诺,尽管他们自己未必意识到。例如最典型的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就有学者指出,同样具有“潜在的本体论特征”。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如果没有某种有意无意的本体观念,那就犹如没有地基或者栋梁的房子、没有根株的树木,根本无法形成任何观念系统,也就无法进行任何陈述。
二、重建本体论何以可能
事实上,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本体论的重建史。既然本体论是必然的,并且解构旧的本体论也是必须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当然就是:怎样建构新的本体论?
那么,历史上那些本体论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 简单说,哲学家面对万事万物,去寻求它们背后的终极根据。问题在于:他们所找到的本体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呢? 人们最容易想到的答案是:这与他们的个体经验有关。其实,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程颢的话:“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里涉及的就是前面谈到的“一”与“多”的关系,即理学家所谓“理一分殊”,亦即“一理”与“万殊”“万事”“万物”的关系。程颐说,“(张载)《西铭》明理一而分殊”;朱熹也说,“《西铭》言理一分殊”。朱熹进而还说:“伊川(程颐)说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及在人,则又各自有一个理。”“‘一实万分,万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处。”“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例如《中庸》,“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简言之,“理一”即那个形而上的唯一绝对的存在者,而“分殊”即所有形而下的众多相对的存在者。
对于“重建本体论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来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旦提出“重建本体论”,就已经蕴含着这样一个观念——前存在者(pre-being、 all the )的“存在”。然而在海德格尔之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里的道理在于:本体是一个存在者;不论是一个什么样的本体,它总是一个存在者。因此,“重建本体论”意味着寻求一个新的存在者来作为本体。但由于本体乃是要为所有存在者奠基的东西,即是先于任何存在者的东西,因此,能够为这个新的本体、新的存在者奠基的,就不能是任何东西、任何存在者。这就是我一再指出的20世纪以来最深刻的哲学问题:存在者何以可能。这个发问方式其实已经蕴含着这样一个观念:“前存在者的存在。”
必须承认,这种区别于“存在者”的“存在”观念,是由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der )率先揭示出来的。按照海氏的说法,哲学长期遗忘了存在,即其所思考的不是“存在”,而是“存在者”;传统哲学缺乏“存在者何以可能”的意识。然而按照“奠基”的观念,如果说形而下的所有存在者都是由形而上的唯一存在者给出的,那么,这个形而上的存在者本身又是何以可能的? “存在者”是由“存在”给出的。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传统本体论为科学等奠基黄玉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图),而他的“基础存在论”为传统本体论奠基。[他的“基础存在论”( )仍然使用的“”,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倾向于使用“ of Being”,以区别于传统的“”。]所以,海德格尔所谓“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意思是由“思存在者”转向“思存在”,这才是真正的“思”。
但是,我也多次指出黄玉本体与超越生活儒学的本体论问题(图),海氏的“基础存在论”也是有问题的。
海德格尔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存在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存在者状态上的可能规定性之外”,那么,存在当然也是先行于此在()的,因为“此在是一种存在者”;但另一方面,探索存在却必须通过此在这种特殊存在者,即唯有“通过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特加阐释这样一条途径突入存在概念”,“我们在此在中将能赢获领会存在和可能解释存在的视野”。如果这仅仅是在区分“存在概念的普遍性”和我们“探索”“领会”“解释”存在概念的“特殊性”,那还谈不上自相矛盾;但当他说“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那就是十足的自相矛盾了,因为此时存在已不再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了。
在上述思考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生活儒学”。简而言之,生活儒学的基本观念就是:生活论或生活存在论为本体论奠基,本体论再为其他形下学(知识论、伦理学)奠基。这是用“生活”来取代和统摄海氏的“存在”(Sein)与“生存”()的区分;而且,这里不仅没有“生存”与“存在”的分别,更没有作为“特殊存在者”的“此在”()的优先性。
简要来说,生活为本体论奠基;或者更确切地说,生活感悟为本体论奠基。这是一种双重奠基的三级架构:生活感悟→本体的观念→万事万物的观念。回到刚才所提到的程颢的话:“天理”是他自己“体贴”出来的;这就是说,“天理”观念的来源既非逻辑推理的后件,亦非经验主义的“主客”关系之下的“经验”,而是一种“感悟”或“生活感悟”,这种感悟是先于任何经验与理性的。程颢能体贴出“天理”,然而孔子、孟子竟然不能,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感悟不同;更进一步追本溯源,则是他们的时代“生活”不同。
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要重建本体论,其大本大源只能是我们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这就必须摒弃任何原教旨主义或复古主义,根据我们自己的新的“体贴”,给出新的“本体”。
三、从“变易本体论”到“超越本体论”
为此,生活儒学建构了自己的本体论:从“变易本体论”到“超越本体论”。
(一)一般性的“变易本体论”
所谓“变易本体论”( ),顾名思义,就是以“变易”为所有一切存在者的本体。“变易”这个观念,来自《周易》。以“变易”为本体,看起来很奇怪:通常的印象,本体总是某种实体;然而“变易”并非实体。但这里的“实体”是西方哲学“”的概念,而非中国哲学“实体”的意思。我曾谈道:
朱熹《中庸章句》第一章题解:“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按照朱熹的哲学,这里的“实体”不论是指的天理(出于天)抑或人性(备于己),都不是说的具有形体或形质的“形而下者”,而是说的无形的“形而上者”。
我们知道,《易传》建构的乃是一种宇宙论的本体论,其本体即“一阴一阳”的“变易”,亦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而“生生之谓易”;这种阴阳变易乃是“形而上者”——形而上的存在者,亦即本体。可以这样讲:“变易”本来并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然而在建构本体论的时候,它被存在者化了,即被视为本体。
我之所以选择《周易》“变易”观念作为本体,是有一番考虑的。前面说过,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本体重建史;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史上曾出现过林林总总的许多本体概念。当此之际,我们要重建本体论,当然可以选取一个新的存在者来作为本体,这不外乎是在上述诸多既有的本体之后,再加上一个新的本体。但是,如果我们试图以一个观念来涵盖上述形形色色的诸多本体呢? 哲学史上的那些本体的相继演替,恰恰就呈现为“变易”,即“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就是《易传》哲学的根本特色:一切皆变,唯变不变。当然,这种“变易”——阴阳之“相摩”“相荡”而“生生”,本来并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即所有一切存在者的渊源;但当我们将其视为“形而上者”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将其存在者化了,它成为我们的观念系统及其陈述之中的最高范畴。
(二)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
最近,笔者提出“生活儒学的内在转向”,所说的就是生活儒学之中形上层级的本体论的转向,即从“变易本体论”转向“超越本体论”( ),意在回归孔子和孟子的超越观念,或者说是新建一个外在而神圣的超越者(the )。不过,严格来说,这其实谈不上“转向”,因为超越本体论与变易本体论之间不是并列与替代的关系,而是特殊或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变易本体论是一般性的,而超越本体论是特殊性的,即上文所说的在哲学史上“诸多既有的本体之后再加上一个新的本体”而已。
超越本体论的特殊性,具体来说就是现代性;这就是说,超越本体论是在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内、特别针对现代生活方式的一种本体论建构。在近来发表的两篇文章里,我对近代以来“祛魅的”()“人本主义”()进行了反思,清算了“人的僭越”,尤其是“理性的僭越”“权力的僭越”。这种所谓“以人为本”的僭越,其实就是“以人僭天”,即“人”鹊巢鸠占地取代了“天”的神圣地位,由此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儒家是哲学还是伦理学,尤其是资本与权力的肆无忌惮以及由此而来的诸多问题,包括近来引人瞩目的科技的为所欲为。
在这种反思中,我特别检讨了孔孟之后的儒家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那种放弃“外在超越”、转向“内在超越”的做法所带来的问题。从宋明新儒学所宣称的“人即天”“性即天”,到现代新儒学所导致的儒家神圣超越之维的彻底丧失,当然有其可以理解的、来自当时现实权力方面的缘由。但是,这样的不再“畏天命”、不再“知天”以“事天”,而是“以人为天”,使得儒家在社会实际的伦理政治关系格局中要么沦为权力的工具,要么被边缘化。有鉴于此,今天的儒家亟须回归孔孟的超越观念,即重建外在神圣的超越者,也就是建构超越的本体论。
编者注:原文刊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及参考文献等内容,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杂志。
由起名专家专业的命理起名平台。